清醒而独立的灵魂—— 忆鲁迅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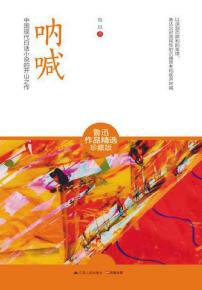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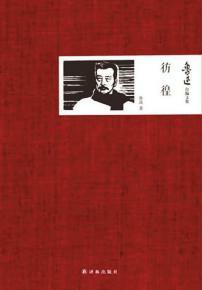
绍兴的酒馆里, 灯光微醺, 繁华与古朴并存的世界诉说着百年前的那一段峥嵘岁月。
至今仍能记起中学时代的课文《在酒楼上》,在先生笔下名叫一石居的酒馆里,他与曾经的友人吕纬甫饮酒话当年, 共谋一醉。
世人眼里的他, 寒意闪闪, 手握烟枪, 尖刻不容人近; 而在我的眼中, 他以笔为匕首,枕戈复待旦,荷戟独彷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先生一直这般,如沉香屑中升起的清烟,坚韧与厚重并存。
少时离乡背井, 而后半生漂泊。 经历过苦难与砥砺、荒凉与萧条后的鲁迅,在并不光滑的世相中,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特殊光华。
清醒者的凄哀
远渡东洋的三年承平岁月,异乡人的嘲弄纷至沓来。在严复 “进化论”的熏陶下,鲁迅毅然弃医从文, 踏上了一条 真 正 能 拯 救
国民的路途。由此,浸润了中国社会数十年的历史悲观主义思想开始在他的脑海里溃散。
然而,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先驱者的宿命大多面临着或抗争或沉沦的抉择, 范爱农就是其中一个。
鲁迅与范爱农在东京留学时相识, 虽是同乡, 初次见面却误会不断。加上身处异国,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戒备。直到辛亥革 命前夕在故土重逢, 笑谈往事, 这才互诉衷肠。
然零星的火光终究抵不过世态薄凉,革命成功后没多久,封建势力便开始复辟,范爱农等有识之士的境况愈发凄苦,范也终至溺水而死。沉浸在悲愤之中的鲁迅写下“把酒 论 当世, 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酪叮, 微醉自沉伦”的诗句,哀叹并肩作战的挚友离去。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 这种清醒者的痛苦是何等悲哀。
穹顶下的呐喊
先生在漫长的黑夜里著书立文,1919 年 4 月 25 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 “夜成小说一篇, 约三千字。” 这就是短篇小说 《药》 。有人说, 先生是在借小说的主人公夏瑜, 以 “握瑾怀瑜,春夏秋冬”隐喻革命女战士秋瑾。 而在我看来, 这更像是一部写给整个社会的小说, 《药》 是鲁迅先生给当时的社会开出的一味灵药,以此来拯救这苦难而麻木冷漠的世间。
凡此种种, 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妻子许广平曾在 《欣慰的纪念》 中提到: “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 长时期在纵酒。” 鲁迅面临的最大压力, 来自于官场和“文人” 之间的抗衡。这种长期敌对的局面让他把忧愁都消解在了酒中, 常常醉眼朦胧。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寂寞彷徨,头脑在半梦半醒间自醉,灵魂却愈发清醒。 “我靠了石栏远眺, 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 有无量悲哀, 苦恼, 零落, 死灭, 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 加香。” 遥遥走过半生, 见证了多少世间的悲喜,仿佛所有的哀愁都化成了今夜的那一盏盏苦酒。
岁月悠悠,鲁迅一袭长袍立于文坛,以诗意的愤慨幻化出声声绝响,又化身奋蹄的青骥,洒下悲悯众生的情 怀 。 如 果 说 早 年 的 先 生 是 犹 豫的—— 因为清醒的革命者往往得不到普罗大众的理解和同情,而经历过此番挣扎过后的鲁迅,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 他深谙于他的“呐喊” 对整个人世间的意义,星星点点的光亮终将汇成炬火, 照亮整个中国大地。
凛冽的天宇下,是先生孤独而有力的呐喊, 何止是 “聊以慰藉” , 字字句句,振聋发聩,无不彰显了他清醒而自由的灵魂。
后时代的希望
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 先生曾怀着 满 腔 忧 愤 , 在《淡 淡 的 血 痕 中》写道: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 有的废墟和荒坟, 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 方生, 将生和未生。” 虽然现世的造物主总是教给他一套 “良民”苟且偷生的办法,先 生依旧相信后来者的勇士终将牵引着新 生和希望向前。
《秋夜》 里的那棵遍体鳞伤, 处于生长起点的小枣树,直指着,伸向夜空, 带着新生的希望, 永不妥协。而弱小如花者, 也还有温情的梦。有战士,有梦, 也就有了希望。 那时烽火漫天燃烧, 民众辗转沟壑。希望从混沌的过往出发, 走遍大江大海, 洒下片片光明。
行文至此,不禁又想起郁达夫先生写给鲁迅的诗句: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绍兴的酒馆里 ,灯光如炬 ,一如当年。
(作者为商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