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报》
清明寄思
作者:肖南屏
2012-04-30
浏览(62)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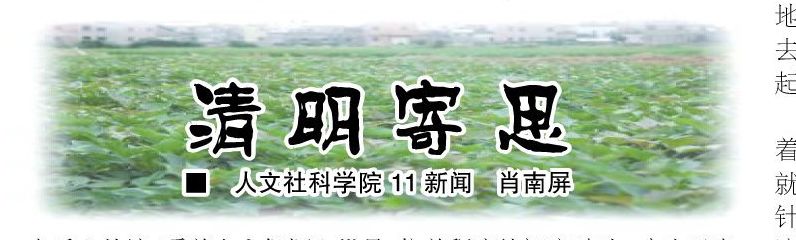
那也是细雨缠绵的时节,奶奶抱着我,坐在老旧的摇椅上,轻声念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窗外的夹竹桃开得灿烂,在春雨的滋润下愈发娇艳。我稚声稚气地跟着念,又不懂什么意思,就在奶奶轻缓的语调中昏昏睡去。
稍大一点我就能跟着大人上山去扫墓了。说是扫墓,不如说是踏青。阳春三月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让人身心舒畅,伸手想摘花,却被大人们阻止了,他们总是表情严肃地说,杜鹃花是先祖的恩赐,摘花就是对先祖不敬。虽然不准我们摘花,但日头一上来,大人们也会扯几条树藤做草帽。我们这些小辈们跟在大人后面,头戴着青草气息浓重的帽子,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跳。
扫墓的工作无非也是除草、放纸钱、刷漆和拜祭。小孩子扛不起锄头,只能做放纸钱和刷漆这样简单的工作。我领到的工作一般是刷漆,先是用小锥子把原来的漆划掉,再用刷子蘸着红漆沿着凹纹小心翼翼地刷上去。这样的工作虽好玩,却很是考究细心和耐心,所以作为女孩的我自然就更适合了。我心里得意,便专注地拿起毛笔,蘸了红漆一笔一画地涂上了,连堂亲们玩儿游戏大声喧闹的声音都没能分散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已满头大汗,用蘸了汽油的毛巾擦去手上的漆,看着大人们摆上供品,依着程序给祖宗磕头,才欢天喜地地拿了饮料和各种吃食,跑到空地上分了去。大人们也不理我们,只是聊起各自的生活近况和祖辈们的往事。
这样的清明节似乎离我很遥远了,已经记不清多少年没去扫墓了。清明假期我总是寻了借口,窝在家里睡大觉或者和朋友一起去玩。堂亲们再亲,也比不上天天一起的朋友亲密,杜鹃花开得再好,也没有橱窗里光鲜的衣服有吸引力,更别说那点吃的东西。清明节———比起春节、圣诞和其他节日,总显得寒酸和乏味。爸妈也不管我,只有奶奶才会年复一年地问我去不去扫墓。我每次都没好脾气地搪塞她,免不了她又一顿数落,说要是她走了我是不是也不愿意去看她。那时候只觉得烦,左耳进右耳出,全然不放在心上。如今想起这些,只觉得十分内疚和懊悔。
每年的清明节都是一出大戏,今年也不例外。各路媒体上充斥着“塞车”“纸iphone”“豪华祭典”这些字眼,我知道这总会消散的,就像清明节的雨,只要太阳一出来,就会停的。但又不像清明的雨,针似的扎在人心上,即便蒸发了消失了,也会留下酥酥麻麻的痛感。这痛感隐匿在身体的某一处,一到“雨纷纷”的季节,便会爬上心头,催人断魂。
我渴望有一只蝴蝶能飞进窗户来,在家乡的传说中,这是已逝亲人的魂灵,千山万水来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