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铁道大学 - 《石家庄铁道大学报》
一部与时俱进的科技史之作
———读 《中 国 科 技 发 展 史 简 明 教 程 》
作者:张宝池 ◇河北省高校关工委工作研究组成员、教授
2008-04-15
浏览(532)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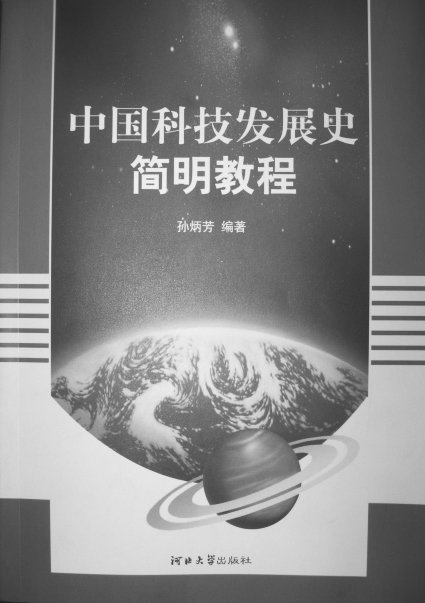
孙炳芳编著的《中国科技发展史简明教程》一书在党的十七大闭幕不久便悄然问世了。本书的雏形是为大学生开设的中国科技发展史课程讲义,经过近10年的教学实践,在博采众家之精华、跟踪时代之步伐、听取学生之建议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
本书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了一个“史”字。这就鲜明地确定本书的学科性质,即它属于史学,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特殊的历史即中国科学技术法。本书以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为历史背景的链条,叙述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使科学技术融入“史”中,又从“史”中溢出科学技术发展之纹脉,进而深刻地印证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的物证,人类历史则是科学技术的符号。”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必须从解读社会生产力开始,而科学技术又是第一生产力,因此没有什么比通过了解科技发展史来认识历史更具体、更生动、更深刻的了。史可为鉴,史可明智,科技发展史尤为如此,这便是本书成功之首要。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突出了一个 “文”字。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是历史母体中的双胞胎。文学艺术孕育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离不开文学艺术。离开文学艺术去讲科学技术发展史就显得苍白无力,更缺少应有的灵性。比如中国古代的陶器、丝绸、雕刻等技术,总是伴随着美术、绘画、造型等人文工艺而产生。创造技术的人往往就是技术和艺术的化身,东汉的科学家张衡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同时还是颇有名气的画家、书法和诗人,还有不少科学家都是多才多艺的。事实说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都以深厚的人文底蕴为基础,科学技术都以一定的人文思想为灵与肉。温家宝总理三次看望“航天之父”钱学森,每次钱老都对总理讲,科学技术离不开文学艺术,二者在山脚分家,在山顶会合。本书突出了人文学科内容的讲述,较成功地实现了文理渗透,为科学技术发展史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无疑增强了教材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本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突出了一个“精”字。本书虽然算不上什么精品,但是“精”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文字精炼、语言精悍、引文精当、节奏精捷,因此这本书写得很薄,只有二十余万字,故不为人所惧,读来朗朗上口,轻松愉悦,有较强的可读性。“精”是古今中外大家们所提倡和追求的文风和学风。中国现代新闻领袖胡乔木生前逢会必讲“要把文章写得精些再精些,写得短些再短些。”朱自清先生讲的更是一语中的,“文章一旦靠近了这个 ‘精’,离‘优’的水平亦渐近矣!”一本书有了好的内容,还必须要有好的形式,只有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可能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尤其是科教论著更应如此,我觉得本书做到了这一点,并没有“讲着科学而违反着科学”,仅此一点就足以对得住读者。在这里我没有使用“学生”二字,而是使用“读者”,显然我没有把书局限于教材范畴,而是将它列入“读物”之类,认为很值得课堂之外的广大读者一读。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使教材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做出微薄贡献,这是当今著述者的崇高责任,更是图书的真正价值所在,本书依稀做到了这一点。
本书的第四个显著特点是突出了史论结合。史明智,论明理。智好比一支蜡烛,理则是烛光。没有蜡烛就不会有烛光,但是有了蜡烛而不去点燃,它永远也不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故智生理,理明智,理智互为依存、相互效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智与理的结合,科技史中更是智与理的统一和融合。本书在讲述科技发展史的同时,又能顺乎自然地升华理性的思考;在理论阐发中又深化着历史,从而做到论从史出,史中寓论,在史论交融中点燃智慧的光芒,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尤其会有效地激发青年学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金无足赤,书无完书。莎士比亚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一切作品中都存在着使自己感到无奈的遗憾。”《中国科技发展史简明教程》中也存在着少许遗憾,比如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分析似乎薄弱了些等,但这无妨本书的整体质量,仍不失为一部与时俱进的科技史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