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 - 《温州大学报》
霍桑的救赎
2008-03-30
浏览(474)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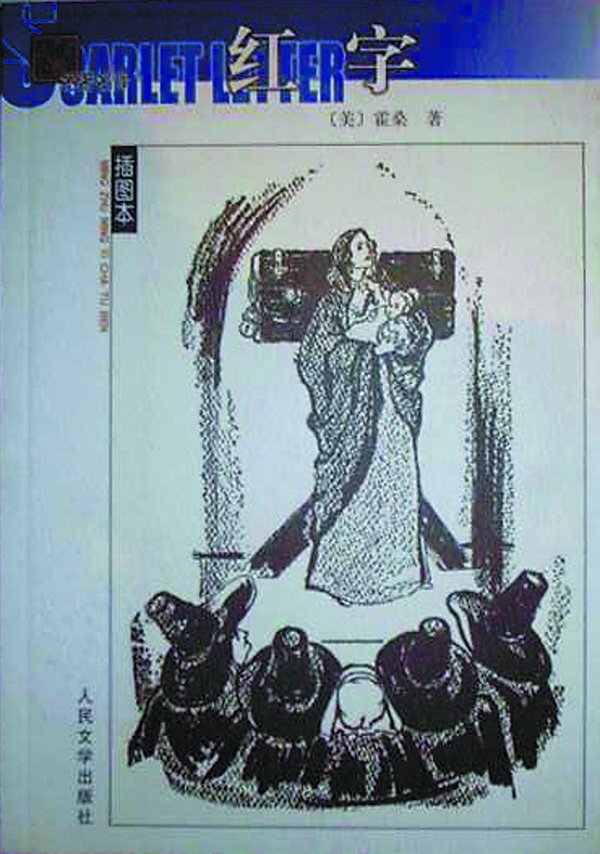
《红字》是一部有关心灵罪恶的忏悔录,而非简单的隐忍的爱情史。尽管霍桑曾经极力想要摆脱父辈遗留 (参与了1692年的驱巫案)的罪恶,然而其世界观中的清教徒意识依然存在并因此影响着他的创作。书中苦苦挣扎的主人公并没有表现出过多超越于历史的自省意识,几乎所有人都沦陷在犯罪与对罪恶的救赎之中,而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
在加尔文教义中,一个罪人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愿望获得赎罪,对他的灵魂的拯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选择”。这也是丁梅斯代儿始终处于一种脆弱无助心理状态的症结所在。作为一个虔诚的牧师,最为接近上帝,甚至被封为圣人,感化了众人却无法拯救自己失足的灵魂,甚至无法对自己的罪孽作出弥补,这足以淹没众人对他的赞美与崇拜,使他的良心受到了更为深刻的谴责。作为一位虔诚的清教徒,他最终选择出逃来重新开始,这从本质上说是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叛逃与否定,所以当他心力交瘁地死在忏悔的刑台上的时候,这个结局其实早已注定。很多人不喜欢书中这个过于脆弱无助的角色,他试图用愧疚填满生命的间隙而从未给爱情留出足以滋长的空间,他难以激起读者对他曾经狂热过的爱情的想象,爱情是他偶尔淘空了自己后拿来慰藉自己的一种寄托。本书的译者曾用“伪善”来标定丁梅斯代儿,事实上它源自人性深处的自私,恐慌与手足无措的自我保护。对于丁梅斯代儿我们应该给他以中肯的宽恕,毕竟这份难以坚守的爱情从一开场就代表着一份难以救赎的罪恶,它被牢牢地嵌在上帝的戒律之中。
所谓罪恶,在书中应该是被完全重新阐释的定义,对于不同的人物都应该具体而微。单单从教义上来看,白兰与丁梅斯代儿的越轨恋情显然是不会得到容忍的,尽管他们共同造就了这段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历史,而两人面对罪恶的态度与方式却迥然不同。白兰·海丝特公开地经受罪恶所带来的惩罚,并通过近乎苦行僧的生活对自己实行救赎,在漫长的七年时光中逐渐觉醒,有了从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自觉意识,一种自由与独立的意识。而正是拥有了这种意识,白兰能够在丁梅斯代儿死后坦然自尊地生活下去,并将那个耻辱的标志A变成德行的象征。而丁梅斯代儿隐藏了罪恶,备受折磨,当他不堪这种罪恶对心灵的压迫,在生命的余辉中决定彻底地忏悔时,他成为了一名殉道者。齐灵渥斯的郁郁而终是对人们慎重的告诫:当一个人的心灵完全被仇恨所占据并不择手段地进行复仇时,他离撒旦也就不远了,这是一个人自我堕落与毁灭的过程———纯粹的罪恶。
霍桑在书中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带有一种复杂的情绪,虽然在书的后半部分它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但就整部作品而言,对于上帝的这种捆绑式的信仰———一方面是对人性的束缚与禁锢,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净化,霍桑并没有全盘予以否定。在这部对人物心理有着如此细微刻画的小说里,白兰·海丝特是一个被还原于真实的人物,她并非是个无所畏惧的女性形象,事实上,白兰·海丝特的心中时常汹涌着波涛,在一种坚忍之中亦然会出现恐惧、动摇、不安。她不止一次地在精神上将自己交由上帝处置而从没有产生过由哪个男人来拯救自己的奢望,信仰成了她灵魂的某种寄托,并使她得到某种警醒,这种警醒时刻引导她在现实中保持勤劳与善良的品质。这成了她的救赎。
书中还有一个最为接近自然人的角色———珠儿,这个遗传了白兰狂野与无畏的孩子安全脱离于宗教的光环并因此保持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性,即便她偶尔会被视为邪恶的精灵。她的身上因为散发着人类自由的气息与野性,时刻保持着一种欢快的状态而很容易受到我们的偏爱。或许她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类的理想状态。《红字》于1994年被改编为电影,而与原著不同的是,电影更着力于爱情引导自由与独立的力量,或许它也是一种与霍桑殊途同归的救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