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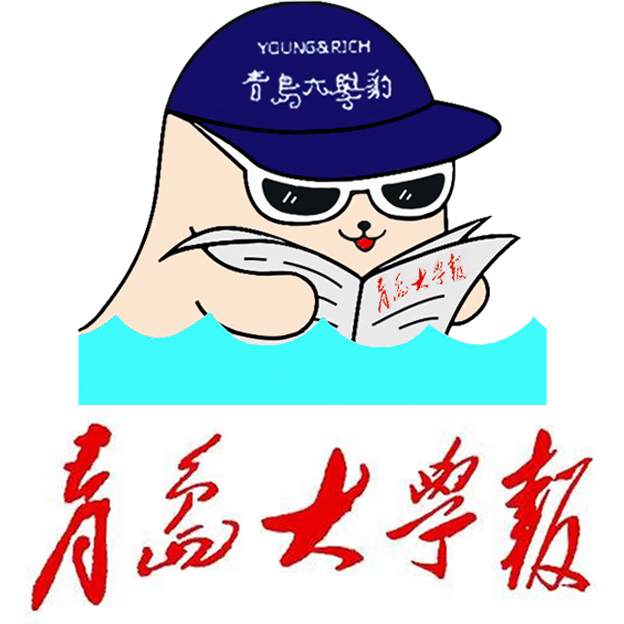
山里的声音是阵阵风声送来的。先是四面八方的风声,吹动树叶哗哗的动静,有人说,那是松涛;拂过草丛的沙沙的声音,有人说,那是音乐。当然,风过耳的,给人或细致入微,或粗壮有力的感觉。你一定会想到交响音乐会的那些不同乐器,弦乐、管乐、打击乐,共同演奏了那些让人落泪的音符。但是,人工的吹拉弹唱,哪有大自然的动听。在山里,风的声音是最强有力的。
春天的山野,偶有细小的花草破土而出,“遥看草色近却无”,诗人与其是看到的情景,不如说是听到了春天的到来,花草突破漫长冬天的压抑,以如此细小的身躯穿透厚土的封闭,那种生命的力量谁能够阻挡得住。这时,你是否会听见一种呐喊的声音,是否会听见生命的歌唱,是否会沉浸于天地会合而产生的美妙的声音。你会感谢风,感谢风的光临,感谢风带来的春的消息,感谢风送来的高天厚土的生命的力量。
风以最清新的气息洗涤着我们灾难深重的双耳,让我们听到了什么是风。我努力在听,想听懂风的语言,我努力在欣赏,欣赏风的节奏韵律。在山间,风与四面的山峦纠缠着,像情侣们的情意缠绵。或者风就是一个多情的人,在你耳上边如此软绵多情地诉说着什么。所谓微风拂面,只是一种肌体生理上的享受,而能听懂风的语言,感受到风的旋律,才会获得精神的快意,才会明白什么叫神清气爽。这时,你可能舍不得疾步走去,尽管你在渴望山峰的高远,但还是放慢脚步,让微风洗耳,静听这些细声曼语。
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风吹过松林,阵阵松涛,奏出悠扬而低沉的低音,风吹过耸立的岩石,高山之上冲上云天的高音让人心动。低音与高音,合奏出美曼而自然的乐声,不由的让人想起了浪漫诗人徐志摩: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诗人的风是有节奏的,如同诗人的感情是跌宕起伏,带有强烈的故事性的。
你一定会想到春天的鸟鸣,尤其在山间,偶尔听到的布谷、鹰雀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飞鸟,让你沉醉于风的境界中,进入到另一天地中。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似的,偶尔的一声“布———谷”,哇……这个哇还没有发出音,就不由自主的停下来,憋在嘴里。突然意识到,再好的词汇也无法描绘鸟的歌唱,再好的音响也无法阻挡风吹来和鸟鸣叫,还不如静静倾听那山里的声音。在山里,在风声鸟鸣面前,我已经失去了表达的能力。“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王维),可惜是在白天的山中,无法体会到“月出鸟惊”的情景;“数叠高山影画屏,一声啼鸟唤春心”(宋·韩淲),这种意境的美也许深藏闺阁中的人更能读得懂,与同是宋代的张玉孃的“帘外落花万点,枝头啼鸟一声”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冬天的飞鸟深藏不出,而一声鸟鸣就能够唤回春的景色。这些诗句是美的,但与身处山野中的旅行者而言,还是不能尽享春天的妙处,也不能倾听飞鸟的青翠。
飞鸟的踪迹并不常见,飞鸟的鸣叫也并不能常听到。这并不是月出会惊飞鸟,也并不是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嘈杂、马达轰鸣、车轮滚滚,人们难以听到鸟的叫声,而是说飞鸟不知何处去,城市的公园、校园的草地,即使山中的树林,偶尔能够看到鸟的身影。我家楼前的草地,偶有几只戴胜、喜雀或其他叫不名字的小鸟在草丛中觅食,不知是因为觅食之累,让它们顾不上鸣叫,还是鸟们已经失去了鸣叫的能力。高高的槐树上的鸟巢间或有飞鸟栖息于此,也多是吱哑几声,宣示自己的地盘而已。
但在山里是不一样的。山里的空气尚还清新,远离马达和车轮,鸟们虽不能放声歌唱,却可以咿呀地叫几声,带给山里的人们些许的欢喜,提振一下登山者的精神气。这时,你可能最想做的,在站在山的某一高处,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叫,那随风而逝的一声撕心裂胆的叫声中,饱含激情,宣泄中带上了哭腔,放情中又有所节制。也许,只有在山野,才会寻到这种释放的方式。
如果不能感受风声,不能听到鸟声,你一定能够听得到山间小溪的流水声。
北方山间的河流大多已不再有奔腾浩荡的气概,涓涓细流中带上了婉转低吟的特点,哗哗流动的河水,像一条飘动的琴弦,让登山者在孤寂中听到了灵动的声音,在近处风声的陪伴下出现了远处或高低,或大小,或哗啦不断,或嘀嗒连绵,或若隐若现,或清晰可辨。它来自于地下,表达了人类最真实可见的灵魂的美,它又是来自于天上。你说,该怎样表达这种连接人的内心深处的音符所呈现的美妙呢。有人说,这是地籁,是的,这是地籁,是源于大地母亲的气息。不过,高山流水,山里的河流是来自于天上的,“疑是银河落九天”,说的就是从天而降的流水,是从天上的银河降临人间的天籁。天籁,那大自然最真实的声音,清澈、柔和、舒适,让人充满了力量。唐代陆龟蒙说:“唱既野芳坼,酬还天籁疎”,这就是天与地合奏而出的天籁。
回到城市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山野里如此静谧的世界里,我竟然遗忘了折磨多年的耳鸣,那种如附在耳边的知了一样的声音,那怕只是山里的那些短暂时光,但我已感到满足。
周海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