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与《辞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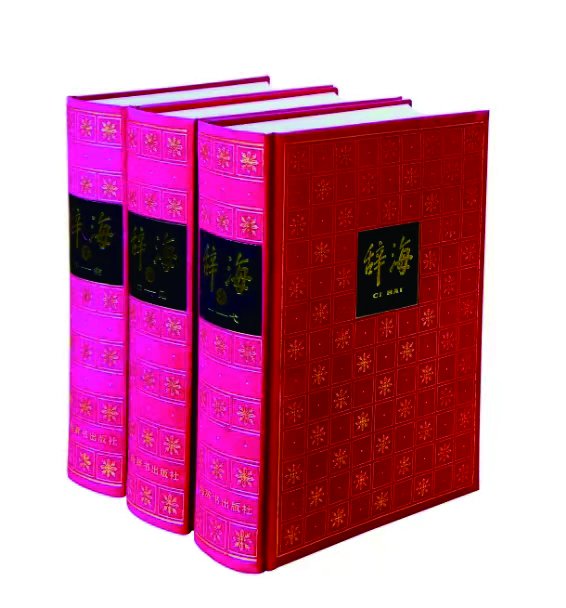
罗竹风(1911—1996),中国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山东平度人。曾历任山东大学军代表、教务长、教授。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任《汉语大词典》主编、《辞海》常务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
“201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并向为这两项重大文化工程付出大量心血的广大专家学者及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看到这则消息,我最先想到的是通读并修改《辞海》的罗竹风先生。
《辞海》是一部以字带词,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兼收,以百科内容为主的大型综合性辞典。1936年出版以来,受到读者青睐,成为广大群众解疑释惑的权威工具书。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读者需求的改变,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36年版的《辞海》亟待修订,而《辞海》以后各版的修订都与罗竹风息息相关。
《辞海》结缘
1957年,毛泽东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这是上海出版局的头等大事。此时,罗竹风任出版局局长。
1958年和1959年,罗竹风力排“左”的干扰,开展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组建工作,从办公场所、人员配备等问题一一落实,拟定了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报上海市委。1959年6月14日,上海市委决定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是指导《辞海》编辑工作的最高决策层,后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1936年版《辞海》的主编舒新城老先生任主编,上海出版局局长罗竹风和市社联秘书长曹漫之任副主编,具体领导《辞海》修订编纂工作。
罗竹风对1936年版《辞海》进行了总结,制定了《修订<辞海>计划》,确定了《辞海》性质、读者对象、词目选收、释文编写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并在凡例中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后经编委会讨论通过,成为《辞海》修订编纂工作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
罗竹风在与专家学者的演练实践中,将修订方针概括为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正面性、知识性和稳定性。提出了行文规则,如对释文的“四至”说,即“东至墙、西至庙、南至沟、北至道”;对释文必须简明扼要的“挤水分”说,将释文精炼到每一个文字和标点;对释文客观表述的“并存”说,即学术观点有几说应一一介绍,这一切为修订编纂工作质量作出了保障。1965年4月出版了《辞海》(未定稿)。这部收词九万八千条,一千一百六十万余字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虽为内部发行,但实际上已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一天晚饭后,罗竹风拿着一叠已经审阅的语词条目,来到语词学组的房间里,跟当时最年轻的编纂者张撝之等,从语词谈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大家越谈越高兴,话题也越扯越远,最后谈到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配图问题。当时有人主张用李清照31岁时的像,此像在王鹏运所刻《四印斋词》的《漱玉词》中,李清照手持菊花,取其词《醉花阴》中“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意。据说此像藏在李清照丈夫赵明诚的老家山东诸城某氏家中。罗竹风认为,李清照的这幅画像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他说:“赵明诚虽然是密州诸城人,但实际上家在青州,那幅藏在诸城某氏家中的李清照的画像又不见著录,且与原本李清照手持兰花的画像不同,自然是靠不住的。”罗竹风接着说:“相比之下,1957年《文学研究》某期发表的李清照的另一幅画像则可靠一些,更能表现李清照作为一位大文学家的气质和风韵。找古人的画像,原本不能胶柱鼓瑟,古时没有照相技术,即使流传的画像也不过是依稀仿佛而已。”张撝之听了罗竹风的分析后,对罗竹风的广博和通达表示惊讶,问道:“罗老,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罗竹风一边笑一边说道:“李清照是咱们山东老乡,又是少有的女作家,能不关心吗?”
从1958年到1965年这七年间,罗竹风自始至终参与了全书的修订编纂工作。他曾协助主编主持召开编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策修订编纂工作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罗竹风用几年时间读完了《辞海》(未定稿)全部稿件。他说:“1962年因为《杂家》问题,我变成修订《辞海》(未定稿)的专职副主编了。虽然没有说明,但自己心里有数,这是‘戴罪立功’的一次机会,于是沉下心来,所有稿子几乎都通读过。有的纵然囫囵吞枣,食而不化,但不管怎样,并非窥豹一斑,而是目有全牛。总算没有白白浪费生命。”任《辞海》常务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巢峰说:“罗竹风既是编纂《辞海》(未定稿)的领导者,又是编纂者、审定者,是用力最多的一个。从头到尾,通读《辞海》(未定稿)全书者,唯罗老一人!”
领导多版《辞海》修订
1978年秋,上海市委作出继续修订《辞海》并出版1979年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的决定。出版局副局长戚铭渠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束纫秋请夏征农担任主编,因为夏征农是老领导,思想解放,又放得开手脚。两人又去请罗竹风出山。罗竹风此时正在等待平反,身上罪名尚在。罗竹风问:“谁当主编?”束纫秋说:“夏征农当主编,请您管具体事务。”罗竹风慷慨应允。
从1978年秋到1979年国庆节《辞海》出版,需要重新组织队伍,做好各种准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总共时间用了不到一年。而从1965年到1978年这12年间,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一次大的修订更加不容易。罗竹风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自主持《辞海》修订工作以来,忙得不亦乐乎,《辞海》修订任务异常繁重,每天约干10小时以上,年近古稀,连续看稿,头即发昏。但由于时间紧迫只好如此。
最困难的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指导思想。客观形势逼着《辞海》编辑部独立思考,拿出办法。在夏征农和罗竹风主持的讨论会上,巢峰说:“还是国际歌中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不如我们起草一个办法。”夏征农和罗竹风对此建议大力支持。在罗竹风直接领导下,由巢峰起草,《<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意见》产生。在1979年初夏的一个夜晚,罗竹风和巢峰一起去主编夏征农家,逐条研究,最后由夏征农拍板定稿。这份文件共有8条39条款。《意见》中的好多问题,现在看来理所当然,但当时却要冒很大风险。当起草时,巢峰的好朋友衷心劝告:“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巢峰把和朋友的话告诉罗竹风,罗竹风说:“编《辞海》没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行吗?‘文王拘,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没有这种精神,绝不可能成就权威巨著。”
在《辞海》这部大书的编辑中,汇聚着近200名专家和100多名编辑组成的高级别人才。如李俊民、贺绿汀、周谷城、谭其骧等,在一百多个学科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该学科的拔尖人,真是星汉灿烂,群贤毕至。初时独缺社会学分科主编,罗竹风决定登门请费孝通担任。他得到了费孝通的支持,并如期完成了该学科条目的撰写和审订任务。罗竹风说:“对历史人物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就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是就是,非就非。”
在最后修订编纂十分紧张的二百多天里,罗竹风始终坐镇一线,帮助解决了许多稿件中出现的尖锐问题,并且为这部饱经磨难的《辞海》撰写了前言。前言中写道:“这次《辞海》修订工作,只经过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定稿、编排和校印任务,这与所有参加的单位和同志们充分发挥革命热情,埋头苦干,日夜操劳,是分不开的。”
1979年9月21日下午,《辞海》出版汇报大会在上海举行,多年来曾为《辞海》埋头苦干、辛勤劳动的《辞海》编委、学科主编、主要编写者以及编辑、校对、印刷工人,1600余人济济一堂。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辞海》走过的曲折道路。汇报大会上,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在讲话中说:“《辞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辞书,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目前的科学文化水平。它的编纂出版,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出版史上是一件大事,特别是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于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罗竹风代表辞海编委会向大会做了汇报。他说:“《辞海》的正式出版是参加修订工作的全体同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所取得的胜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专程赶来参加会议,并代表国家出版局和首都出版界对大会表示祝贺。
1979版《辞海》全书选收单字14872个,选收词目91706条,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所收词目,以解决一般读者在学习、工作中“质疑问难”的需要为主,并兼顾各学科的固有体系。释文要介绍基本的知识,力求简明扼要,并注意材料和观点的统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疑问,查《辞海》”。
1979年版《辞海》出版后,罗竹风就提出,《辞海》应过若干年就修订一次,辞海编辑委员会也应一直保持下去。这些意见对保持《辞海》修订工作的连续性起了重要作用。随后他对1989年版的工作,提出了继续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力求反映最新的科学文化技术成果、搞好补缺纠错删滥三项意见,并为1989版《辞海》题词“去冗补缺,精益求精,质量为重,面貌更新”。这些意见经编委会归纳补充和整理后,成为指导修订工作的总要求。
1989年版《辞海》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较1979年版跃上一个新台阶。
1994年3月巢峰把起草的1999年版《辞海》编辑方案送给罗竹风审定。罗竹风在病床上审读这一方案,仍然一丝不苟,字斟句酌,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修改订正竟有49处之多,最后批上“请打印上报,罗竹风。1994年3月31日”。1996年在华东医院的罗竹风与夏征农、苏步青、周谷城一起向上海市委报告,提出1999年版修订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总体构想。1999年出版的彩图本,告别了以往那种白纸黑字线描图的传统形式,成为《辞海》更新换代的标志。
1995年,当罗竹风获知《辞书研究》编辑部要出版纪念《辞海》出版六十年专辑的消息后,竟不顾病痛的折磨,主动提出撰写《<辞海>六十年》,为后世留下历史记载。文章详尽回顾了《辞海》从1936年问世到1996年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对各个时期《辞海》编辑情况作了论述和总结,是一份反映全貌、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理论性、科学性很强的历史资料,这也是罗竹风为《辞海》编纂事业作出的最后工作。
“辞海精神”
在1989年版《辞海》问世前夕,江泽民同志欣然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他把“辞海精神”概括为12个字: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这是《辞海》编辑工作中逐渐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普通词典学理应给予极大关注的根本原则问题。词典是规范性出版物,读者视之为无声的老师,寄予高度的信任。这就是“有疑问,查《辞海》”出处。只有发扬“辞海精神”,才能把词典编成名副其实的规范性出版物,否则就难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作为《辞海》常务副主编的罗竹风,始终是“辞海精神”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他说,辞书不同于一般图书,更不同于报刊。基本原则应当是:准确而又简明地给读者以具体知识,释文应恰如其分地如实反映对象的实际,最好以原始资料加以说明。要避免想当然和无根据的论断。介绍稳定性的知识,是辞书最根本的任务。他在祝贺1989年版《辞海》修订出版时,写下“去冗补缺,精益求精。质量为重,面貌更新”。
罗竹风说,对于稿件,要像况钟断案时的千斤笔那样,不轻易下笔修改,意见用铅笔、浮笺标明,以便相互研究。要多思考,多揣摩,然后再决定怎样处理。他又说:“修订《辞海》是一项重要科研项目,必须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决不能掉以轻心,潦草用事。”凡是参加《辞海》修订工作的同志都有深刻的体会。辞书编辑工作,正如采花酿蜜一样,占有了大量材料之后,还得有所甄别,决定取舍,言简意赅,正如“浓缩铀”,它本身所蕴含的能量是无限的。一个辞书编辑工作者应当凛然于责任的重大,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大量材料经过抉择,取舍得当,材料与观点相结合,凝结成少数文字的释文。其中既不能掺水分,又不准有杂质。
罗竹风已把“辞海精神”带到生活的细节中,他与全体辞海人用辛勤汗水铸就的“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必将引领一代代辞海人勇往直前。
(作者系青年文史学者,著《罗竹风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