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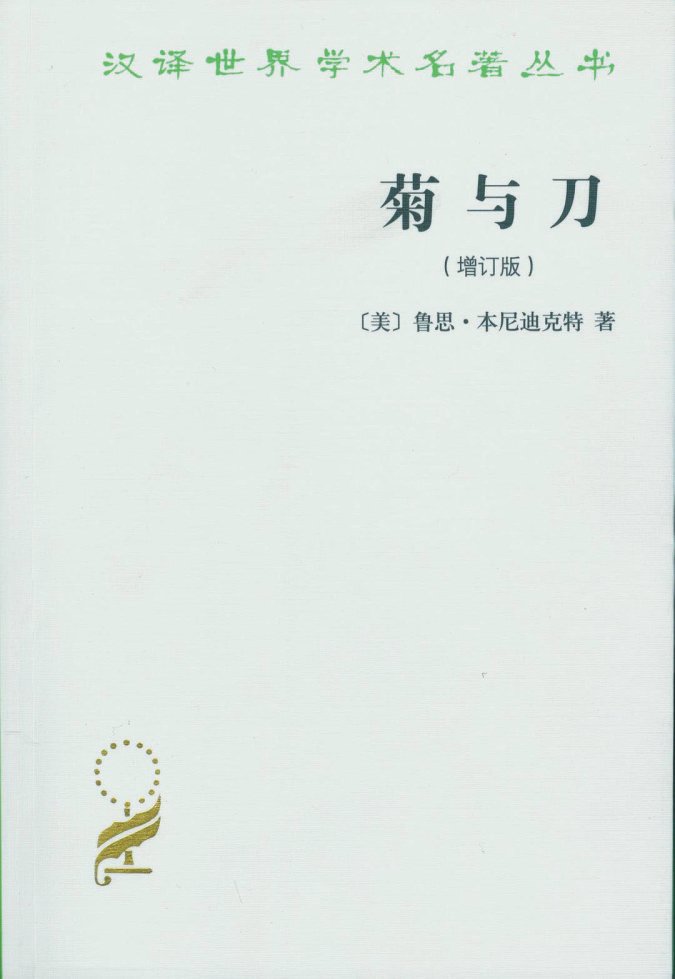
《菊与刀》是一本让我拓宽格局的书。作者是鲁思·本尼迪克特。
这本书有其独特的创作背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同是欧洲文化背景,美国对德国战后问题的决策较为清晰。但是如何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问题,美国政府需要迫切作出决策。为此,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以期制定出最后的决策。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接受这一课题的众多专家学者之一。她是一位美国女人类学家,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后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并取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主要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
当时日美还在交战状态,本尼迪克特不能到日本本土进行调查。于是,长于田野调查的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战犯,同时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特用“菊”与“刀”的形象,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民族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即《菊与刀》。
此书的第一章是方法论——研究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在这一章里,我初识了“人类文化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也初识了作者。仅读这一章的功夫,我就深深迷上了这门学科,同时,我也深深地折服于作者的文思。
在后面几章里,我重新认识了“日本”这个我自认为耳熟能详的国家。作者在书中详尽论述了日本的等级制、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修养、儿童教育,论据充分且栩栩如生。尽管关于日本的一切都让我感受到“距离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作者似乎也深知这一点,于是她用了很多的“手段”让我相信,或者说,让读者相信。她用了大量的对比,用的最多的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比对”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对”。这些对比的运用妙就妙在,它们先是让我相信文化的差异,再让我相信日本的确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国家。于是,顺其自然的,我认识了作者笔下的(当时的)“日本”,并大受震撼。
不得不提的是,我非常喜欢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这段话:“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们看来就是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还有这段话:“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及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坚信,“矛盾”就是作者对日本的第一印象,虽然我不知道事实怎样,不知道当今的日本人是不是也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那样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理解了日本人的“矛盾性”之后,再去理解他们的各种行为与理念,就容易多了,而且的确是合乎逻辑的。
除了倾尽所有地描述上述的第一印象外,作者还在书中用第五章和第六章描绘了日本的另一显著特征——对“恩”的重视与讲究。而这也重击了我原本的三观,因为在“恩”这件事情上,我更偏向于美国人的理念,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而是自由给予的——但“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债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意是负债。);‘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地偿还。”
“在日本,人们在受恩时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债。但是,恩债感又是很难忍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读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总是眉头紧锁的。一部分是因为难以理解,一部分却又是出于同情,而后恍然大悟,我也是”矛盾的“,或许每个人都是矛盾的??
(本报文艺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