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歌唱
——对话“花地文学榜”金奖得主
今年3月,羊城晚报评选出2015“花地文学榜”六位金奖得主:毕飞宇、笛安、沈苇、王跃文、筱敏、李敬泽。这些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水准的作家和批评家,于3月29日上午空降华南师大,与华师学子畅聊“文学与人生”,现场座无虚席。华南师大报也借此机会对话金奖得主,感受一番思想碰撞出的火花。
写在乡村与城市边上
生活不能尽然于文学中,但文学来源于生活,于是乎,作家用文字构造出的世界多少会沾染了些现实世界的色彩,就像作家作品中的“文学故乡”与其现实的故乡。或表现乡愁,或仅仅是潜意识里将故乡当作是作品中故事展开的背景,或是文字表达沾染地方色彩……人性的一半是地域性,文学的一半是地域性,这种地域性让人成其为人,让文学不至于千篇一律,是不可抹杀的。但是文学寻找的是地域性之下的普遍的人性,地域性不应成为写作者的囚笼。

王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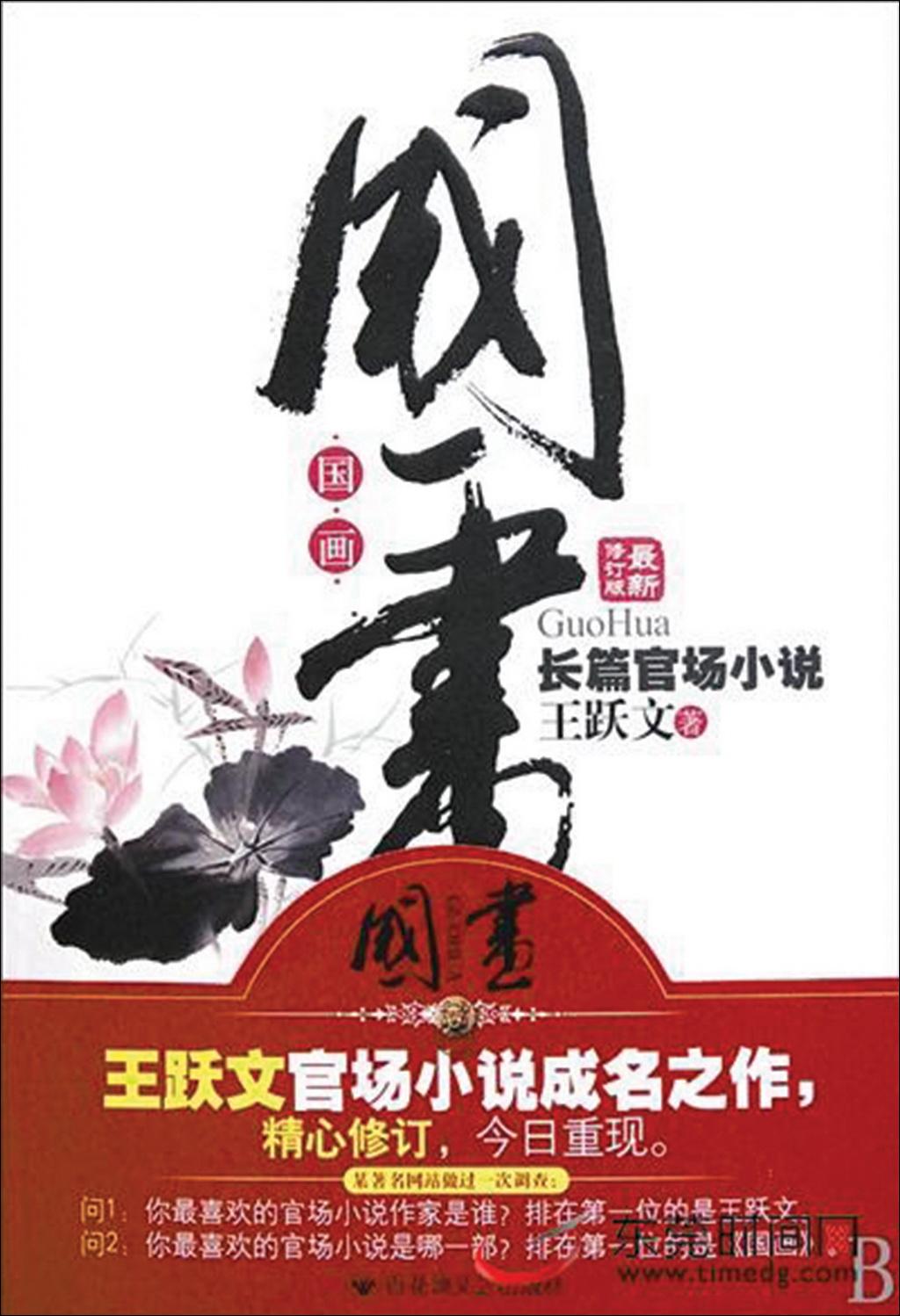
王跃文作品《国画》
华南师大报:除了书写官场,我们还注意到您的作品里有一种乡土情怀。
王跃文:乡村的生活在我的小说里面是有反映的。我也写过很多乡村小说,比如去年获过鲁迅文学奖的那个《漫水》,写的地名就是我自己家乡村里面的地名,写的那些生活也是我记忆当中的乡村的生活。写作的时候,最让人感到痛快的就是写完以后心里很安稳、很安慰、很温暖。我在我过去写作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因为写完一部作品而失眠,唯一一次就是《漫水》写完了的时候。当我写到了里面的主人公之一,惠阳的一个老人,被村里的人抬走,像是有一条火红的飞龙在驾着他慢慢地升到天上去。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泪流满面,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所以乡村生活,我们家乡的这种生活对我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非常得意或者说感到自豪的,就是有一个“乡村”作为故乡。我觉得一个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有这么一个“乡村”作为自己的故乡,而且能成为自己的“文学故乡”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华南师大报:您提出可以在文学方面首先尝试“留住乡愁”,保护传承传统文化。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做?
王跃文:不同的人对于文学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像我们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一样。其实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和对生活的不同理解是一个意思,没有对错之分。所以说当我有这么一个乡村的故乡,我对它当中所存在和承载的一些美好的传统和文化比较醉心,那么我通过文学来呈现的时候,我会感到很高兴,很幸福,会有成就感。我觉得通过文学来呈现乡村的这些传统美好是非常有意义的。

笛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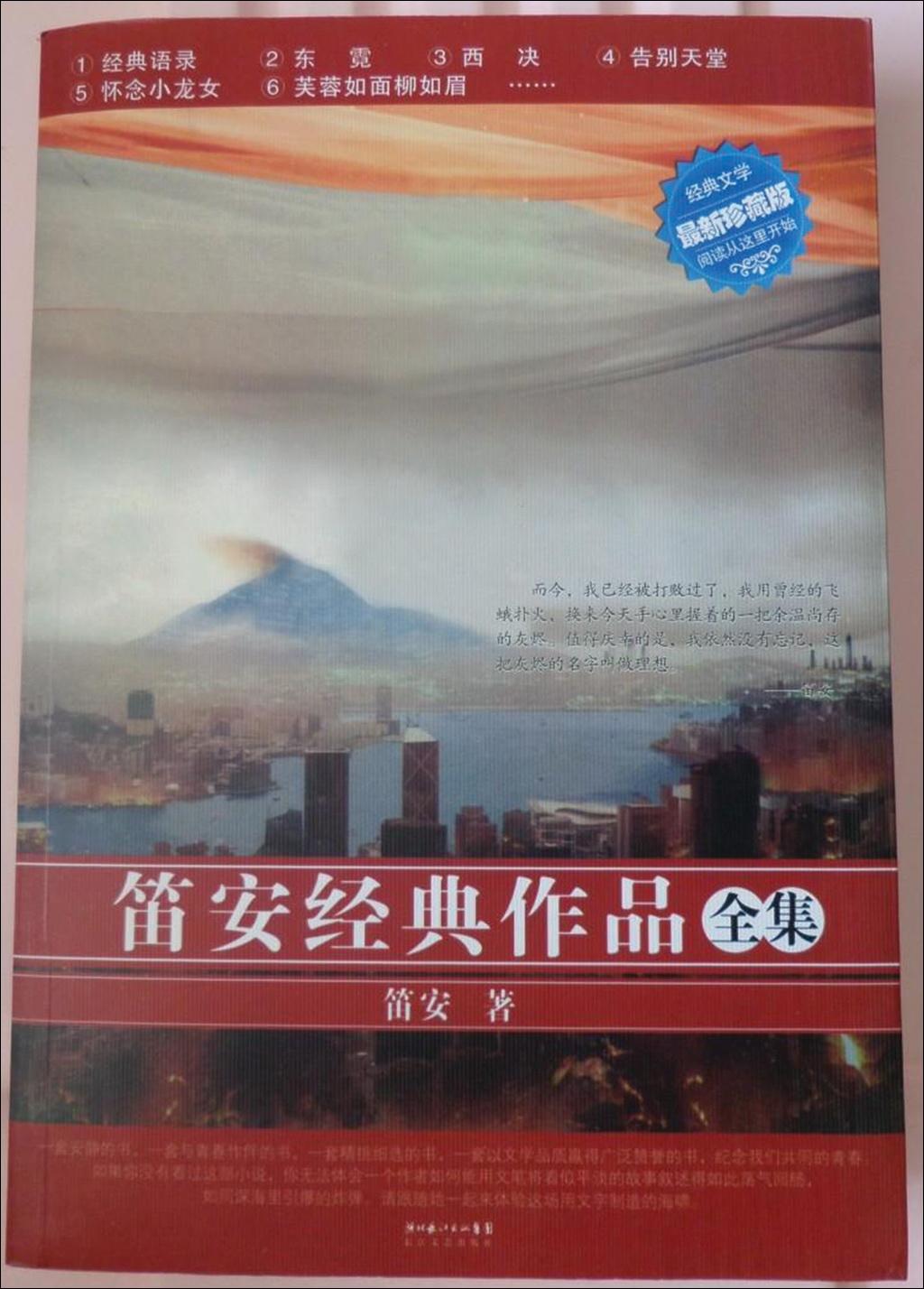
笛安经典作品全集
华南师大报:您的书里经常出现一个春天里充斥着沙尘暴的工业城市,那是您故乡的缩影吗?
笛安:我的小说绝大部分背景确实都发生在一个春天里充斥着沙尘暴的工业城市,我确实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长大的。故乡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比较复杂,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是在这个地方长大,我们家也经过好几次的迁徙才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对这个地方的认同和归属又有一点复杂。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乡愁只是我一个人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等式——乡村等同于文学作品中的美好,而城市就是各种各样不好东西的集大成。如果有人这么想我也不能说他错,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我觉得城市是美好的,我任何的小说作品都这么坚定地认定了这个。从小成长在都市,其实都市里的乡愁也是非常复杂有意思的东西,而且属于城市的这种精神归属和审美也是我们现在的作家应该去探讨的东西,当然,这个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沈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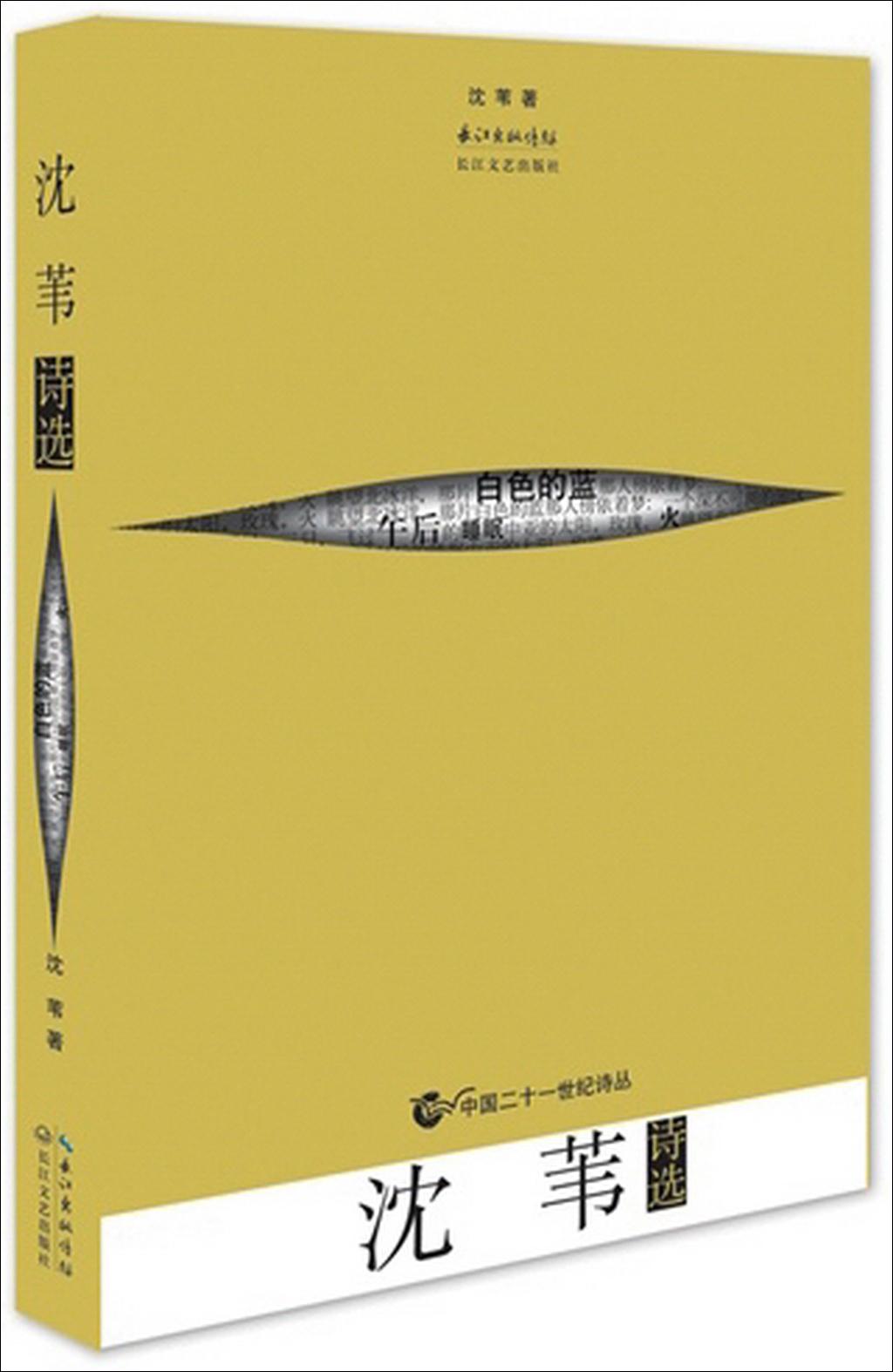
沈苇作品《沈苇诗选》
华南师大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新边塞诗”曾一时风光,您也被冠以“新边塞诗人”的名号,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身份的呢?
沈苇:在当代文学史里面,新边塞诗可能是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概念。所谓新边塞诗,就是西部诗,有三剑客杨牧、周涛、章德益。但是这种概念还是非常空和大,它其实遮蔽了一种具体的写作。所以我也曾经在文章里写过说我不是西部诗人,也不是新边塞诗人,只是一个此时此刻生活在新疆或者生活在西部的一个诗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概念里面,我们应该更关注一些具体的诗人,或者具体的作品,就像现在大家在关注余秀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事。从八九十年代大学生们关注席慕容、汪国真,到现在关注余秀华,意味着中国读者的一种进步,读者的一种水准和鉴赏力的进步。
我曾经把新边塞诗比作一个羊圈,这个羊圈里面男的老的黑的白的胖的瘦的羊都被装到一个羊圈里面去。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羊圈,拥挤不堪的羊圈。但是,在这个羊圈里面发出的羊叫,它不是一种合唱,在合唱里,你可能更应该关注一只具体的羊的具体的独唱。
华南师大报:您曾在作品中提出人性是大于地域性的,那么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性是如何理解的?
沈苇:我是南方人,大学毕业也后到新疆,是个跨地域的人。我把之称为“地域分裂症”,我把自己比喻为一只破皮球,被江南与新疆两只脚踢来踢去,只有写作,才能治愈我的分裂症。说起这个问题,我想起了美国某位诗人的一句话:人的个性的一半,是由地域性造成的。人生在那个地方,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这个故乡的无法选择,因此造成了人身上的地域性,人性的一半是地域性,人的身上永远带着这份地域性。但是文学的功能并不是迷恋这样的一份地域性,文学的功能就是要找到地域性,人的身份,民族、国家的身份之下普遍的人性,这是一种超越的人性。我们今天的小说家也好,批评家也好,青春文学的笛安也好,我觉得都是在寻找这种人性。
用文字叠成一个世界
文学创作就像是唱歌,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想唱时还是会去唱的。可是用文字架起的世界和用音符谱成的世界终究不大一样,因为前者指向性太强了。多亏这种强烈的指向性,写作者得以切肤地表达自己。运用文字恰到好处地建构起在脑海中显现轮廓已久的文学世界,这十分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

毕飞宇

毕飞宇作品《玉米》
华南师大报:您在《青衣》、《玉米》等作品中都有对女性心理的很细腻的描写,您也被誉为“最擅长写女性心理的男作家”,请问您是如何出色地做到这一点的?
毕飞宇:我觉得一个作家首先要具备一种基本能力,那就是塑造人物,塑造人物的时候是不能思考细节的。如果你说某个人物形象没有塑造好,我会跟你说这个小说家有基本的缺陷,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小说的人物塑造得好,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想我还是会把它归功于我写作的能力。
华南师大报:在您的作品里,像《青衣》的筱燕秋,《推拿》的都红,您对于表现当代人现实生活的疼痛这方面的内容好像情有独钟?
毕飞宇: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弱者,所以在写作上、虚构上侧重于这方面,我对这种人的情感认同度更高。那些表演的,拉二胡的,一般来讲,热衷于艺术的通常都不具备一个强者的身份。所以呢,我对于那种有艺术气息的人的关注和偏爱本质上来讲也是我对艺术的偏爱、我对弱者的偏爱。这是我的人生观。
华南师大报:您曾在访谈中说到,“技巧是写作的兵器,你一定要去淬炼它”。那您是怎样淬炼“兵器”的?
笛安:在写作时,对于两个情景之间怎么衔接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变态的执着,我会为了这一两百字的衔接而死磕一天。这个场景之间的转换实际上特别考验一个作者的功力,写小说毕竟不是写剧本,不能永远依靠另起一章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场景。
我觉得俄国十九世纪小说家把这种技巧淬炼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尤其是这种传统的叙事。技巧肯定不是终极目的,但是当技巧这个东西真的开始让你熟悉、深刻进入并跟你的身体合二为一的时候,他们帮助你更自由地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事。

李敬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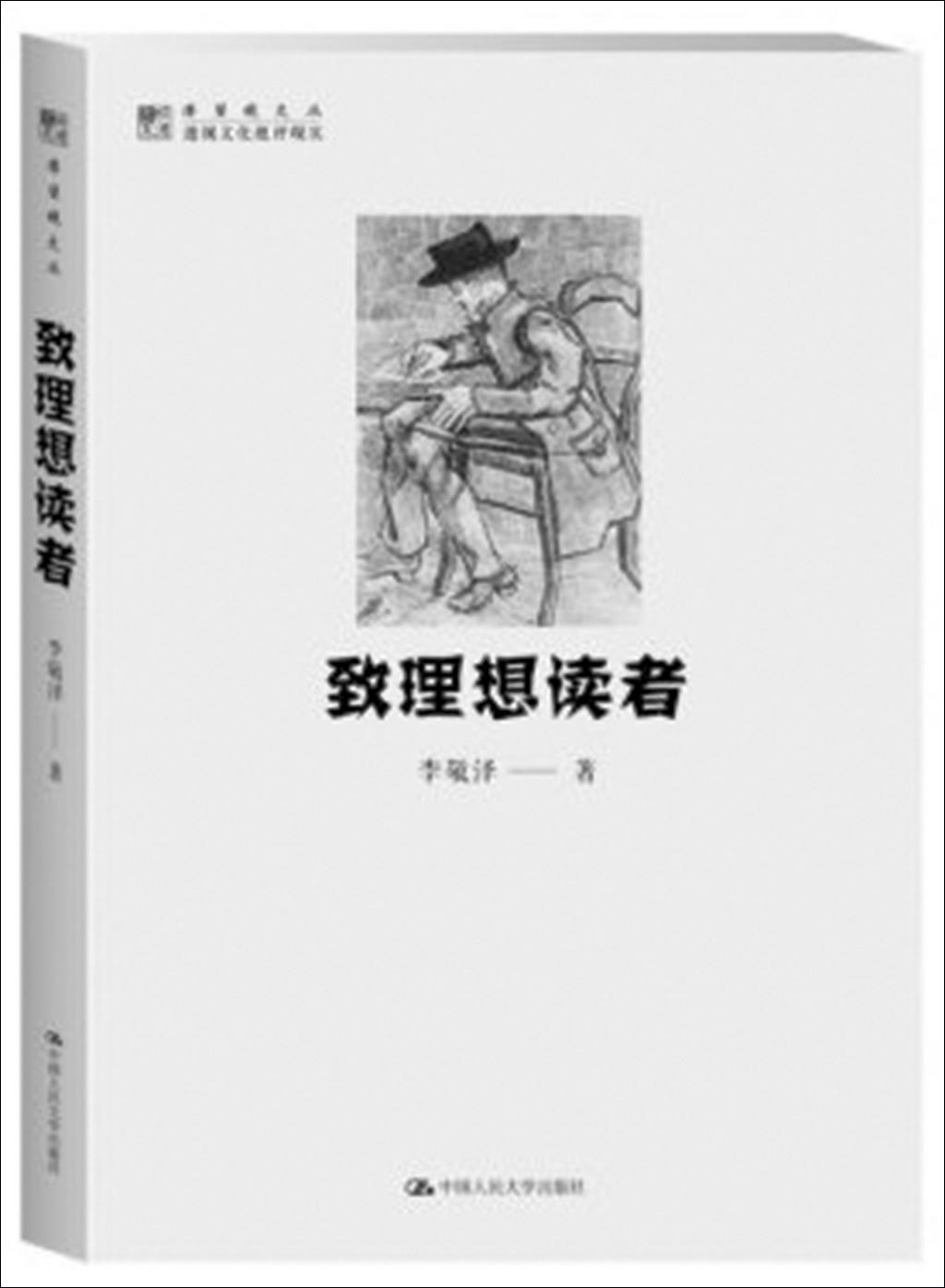
李敬泽作品《致理想读者》
华南师大报:作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您能跟我们说说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吗?
李敬泽:总的来说,创作与批评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对象:人性与人类生活。创作以感性的语言表现作者对人性与人类生活的理解。批评虽然以作品为对象,而且更注重理性思维,但其目的同样是通过观察作品、升华并呈现人的生活,批评也是一种创作。因而两者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本报记者 全晓欢 黄秋华 姚梓晴 黄淳 谭婉玲 林君艺 吴炫 莫月琳 陈晓绚 李雪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