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川外廖七一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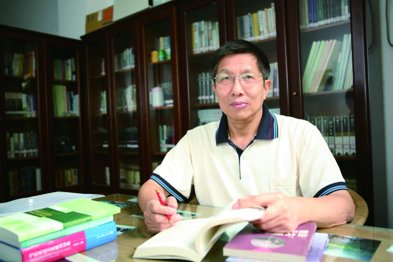
不久前,得知我的研究生同学苟欣文调川外任职,我请他方便时代为问候廖七一教授,并简单讲述了我与廖老师之间的交往。这是我珍藏心底的一段回忆,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和感恩,是对人世间一份温馨美好情谊的珍惜与感动。正巧川外编辑校庆70周年文集《川外·川外人》,欣文建议我把这段往事写出来,作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川外的补充。我欣然应允,却迟迟未能动笔。那是因为,一旦打开思绪的闸门,回首往事,我便热泪盈眶,情难自禁……。
初识廖老师,是1987年在我市沙坪坝区新立小学开设的川外英语培训夜校的课堂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早早辍学,没有正规学过一天英语。对于已过而立之年在党校任教的我,当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报考研究生,继续学习深造以适应工作,而考研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英语。为此我已用几年时间,自学了初中、高中到大学许国璋英语教材第一、二册,但学到第三、四册时明显感到吃力了。这时,看到川外夜校开办许国璋英语第三、四册辅导班的消息,犹如雪中送炭,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英语学习。每到上课那天,我下班后给刚放学的儿子买一个面包当晚饭,然后带着他匆匆乘坐2路电车从歇台子到沙区新立小学上课。
给我们上课的,是川外的廖七一老师。那时的廖老师年轻气盛,精神抖擞。课堂上,他深入浅出,挥洒自如。课下,他与同学们谈笑风生,随意平和,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来上课的同学除了我全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我总是自觉也有些自卑地带着儿子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排。每次上课不到一半,儿子就趴在课桌上睡着了。
一天课后回家路上,我背着照例已睡着的儿子跟在同学们后面。廖老师走到我身边,与我边走边聊。他问我:“来补习的年轻人多为考托福出国,你这么辛苦是为什么呢?”廖老师的关心一下触动了我,我忍住心酸,简单讲了讲自己的情况,聊起来才知道我的父亲与廖老师的父亲竟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无须多言,共同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仿佛在一刹那间达成了彼此的理解,拉近了我与老师间的距离。我为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廖老师已是大学老师而自己还在补习ABC而惭愧,可善解人意的廖老师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优越感或怜悯之意,他真诚的目光和不多的话语里,是满满的赞许和鼓励。廖老师说,今后,无论你考上没有,都告诉我一声。从此,在我艰辛的求学路上,又多了一份来自素昧平生的廖老师的动力。
1990年,我参加西南三省一市研究生招生统考,作为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考生,在有不少大学本科生参加的角逐中,我考了英语第一名。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如约给廖老师去信报告,这时才发现,我所有的关于廖老师的信息只有五个字:川外,廖七一。去信后,迟迟没有回音,我想也许是地址不详,也许是廖老师知道就行了,不回信也正常。没想到好几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来自川外英语系的一封厚厚的回信,原来廖老师出国访学一年,回国后刚看到我的信。
廖老师的信字迹潇洒,富有文采,字里行间充满热情的祝贺与鼓励,感受得到是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这封信我读过很多遍,以至信封都磨破了。可惜由于我太过珍惜,专门收藏,却因为藏得太好后来连我自己也找不到了,令我十分遗憾。信中有两句话我记忆犹新:一句是表扬我的求学精神,“当今社会,……(对学习)像你这样执着的已不多了”;一句是鼓励我坚持自己的学习追求,“达则兼善天下,退而独善其身”。这两句话,因被我时时用来警醒自己而铭记至今。
后来,我研究生毕业了。再后来,我当了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校研究生部主任。我带的硕士生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每当看到他们学习的刻苦坚韧,生活的困难艰辛,我常会想起廖老师当年是怎样对待我的,我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一点小小的关怀帮助,对此时的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莫大的温暖和鼓励,正如廖老师当年对我的一次询问、一封信……。
说起与廖老师的缘分,还有两件有趣的事情。
一次是2003年,我在工作中接触到我市学位委员会委员名单,才知道廖老师早已不是原来英语系的一名普通教师,而是我市学位委员会委员、赫赫有名的英语专家,各种学术成果、学术头衔和行政职务一大堆。我不禁为廖老师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为廖老师严谨谦逊、真诚朴实的人品,深深感慨,肃然起敬。那一年,我曾陪同我校副校长,为我校硕士学位教育问题专程到川外拜访廖老师。乍一见面,我差点没认出来。当年讲台上那个开朗活跃,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如今坐在我面前,却是一个温文儒雅,老成持重的学者。但那份谦和,那种微笑,依然熟悉。廖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临走还送我一册他刚编著出版的精美专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作为纪念。这是我与廖老师夜校分别16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还有一次,是2009年在我市社科联召开的重庆市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我在获奖目录中看到了廖老师的名字,他与我分获市政府二等奖和三等奖。但我用目光搜索会场,却没有发现廖老师。散会后走出会场,忽听有人叫我名字,回头一看,廖老师正微笑着站在路边,用略微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说怎么看上去跟过去不太像了呢?后来想了想,可能是因为参加颁奖大会,我精心收拾了一番,身着职业套裙登高跟鞋,还淡淡地抹了一点口红,与当年背着孩子疲惫不堪蓬头垢面的样子反差较大的原因吧。这是我与廖老师自夜校分别后的第二次会面,距那时已过去了22年。
2012年春节前夕,我出版了自己的业余习作《江山重庆》诗画册。我给廖老师寄去一册拜年,并在扉页上写下一首小词,表达多年来珍藏心底的感激之情:
采桑子·致谢廖七一老师
携儿夜读承怜问,泪洒心田。不忘赠言,求索登攀未敢闲。
才华人品皆师表,仰止高山。常忆从前,滴水之恩当涌泉。
廖老师很快回赠我一张精美的贺卡,并在上面写到:
王老师:
岂敢妄为人师!
二十五年前,王老师不安命运的安排,不惑不忧不惧,着实让我受到鼓舞。二十五年后的今天,王老师的成就与境界,让人感叹之余又深感惭愧!
感谢馈赠精美的画册。恭祝王老师新春快乐,事业发达,阖家安康!
——廖七一於2012岁末
又一次看到那潇洒的笔迹,又一次读到令我鼓舞给我启迪的话语,仿佛又见到了当年那个叮嘱我考研后务必将结果告诉他一声的廖老师……
行文至此,一路梳理下来,我发现我与廖老师除了上大课,面对面的交流其实一共就只有上述三次,加起来可能不到半天时间,但这种交往却影响了我一生,这份敬重与感恩我珍藏了一生。今天,离当年夜校初识已过去了整整33年,我与廖老师也都从中年进入了老年。但这份朴素而深厚的师生情谊,铭刻于心,温暖如初。
岁月沧桑,师恩难忘。想念廖老师,感谢廖老师,感谢川外。
本文落笔之日是七月一日。是我们党诞生九十九周年的日子。我突然想到:莫不是廖老师名字中的“七一”正是指的今天吧。冥冥之中真有这么奇妙的事吗!衷心祝愿廖老师阖家安康,一切都好。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生部原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重庆市第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