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报
方立天:在佛教和哲学两块园地内“双耕”
作者:■方立天
2013-05-27
浏览(76)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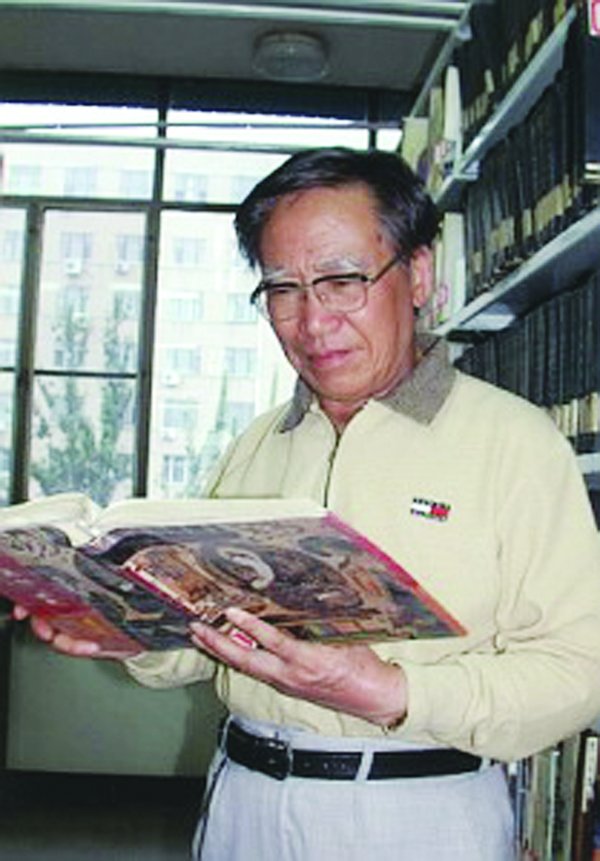
方立天(1933—),浙江永康人。著名佛教研究专家、中国哲学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
三个重大转折决定我的生命历程1933年3月,我出生于浙江省中部的一个农村:永康市四路口中村。我的家乡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幼年时,我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可是时运不佳,由于日寇的侵略,我的家乡屡遭践踏,致使小学上课时断时续,没能连续地把小学念下来。1946年春,我开始在永康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49年毕业时,我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被时代车轮带进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工作。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得以较早地投身革命,经受革命锻炼,这是我人生第一大转折。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等院校。这一年的秋季,我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二大转折。从1956年入北京大学,到1961年大学毕业,可以说是我学术研究的“准备时期”。在北大的学习,为我以后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北大五年实际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当时一有空,我就扎到文史楼阅览室看书,由此也养成了一个终生受益的习惯,这就是泡图书馆。后来到人大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我端着一个水杯,背着一个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学习备课、研究写作。
1961年,从北大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转折点。自那时起,我在学术生涯的漫长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我决心把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在这两块园地进行“双耕”,这成为我相当长岁月里学术活动的基本内容。
大学毕业时,我的佛教基础知识是很有限的。为此,我于1962年到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佛学院进修了八个月。在佛学院进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不小,主要是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历史和理论的基本知识,对僧人的生活实践也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感受。
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后,结合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我开始了佛教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文革”后,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下,我的佛教研究工作又得以继续,按原来的设想并结合实际的需要而有计划地进行。回顾昔日人生历程,我一直生活在社会不断大变革的不平凡的岁月里,深感个人命运与历史演变密切相连,个人的学术活动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工作了5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宗教学研究重镇。是中国人民大学为我提供了研究的机会。多年来,我朝着理想努力工作,终于在21世纪初被教育部选中为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的带头人,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各种荣誉,2009年被学校聘为一级教授。
我的佛教研究轨迹迄今为止,我着意研究的佛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思想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今译,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反映了我的佛教研究的轨迹。
(一)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思想的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中,我比较注意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和佛教思想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去揭示佛教思想家的哲学内涵和思想特色,评价他们在佛教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又通过佛教思想家的典型思想,凸显当时的佛教思潮和整个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我先后写出支遁、僧肇、萧衍等人佛教思想的论文。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了我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后来,我又撰成《慧远及其佛学》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此外,我还撰成《法藏》一书,1991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二)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要科学地研究佛教思想,最重要的是要读懂佛教典籍,深知其意,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读懂佛典,把握其中所包含的意蕴,绝非易事。认真做一点佛典的整理工作,是有助于提高阅读效果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基于此,我做了一点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如,和几位师友就中国佛教的重要典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标点,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多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我还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应约在原来校释的基础上,将原文译为现代汉语,撰成《华严金师子章今译》,由巴蜀书社出版。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是一种重要的专业训练,在切实把握佛教思想方面,对我产生了良好而持久的作用。
(三)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尝试1986年,我的《佛教哲学》一书问世,后经扩充于1991年出版了增订本。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它列入“人文丛书”再版。我在《佛教哲学》一书中着重于如实地勾勒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我认为,佛教哲学主要是由人生观、宇宙观、伦理学和认识论等方面构成,这几个方面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是否善于运用多元化的正确方法,对佛教哲学现代化的成功研究有着重大关系。在撰写过程中,我注意从实际出发,力求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并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结合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述方法。在论述中,竭力排除主观好恶,淡化情感色彩,努力多作客观平实的分析和叙述,并且着重挖掘其特殊的价值和贡献,认真揭示其失误与流弊,力求做到辩证分析,实事求是,合情合理。
(四)佛教文化研究的开拓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不可避免地与现今人们观念深处的传统文化劈面相撞。学术界的历史使命感和探索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升华,于是一股强劲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随之兴起。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我也产生了探索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强烈冲动,撰写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由长春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我在书中指出:“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用层次和结构的观念来理解、把握佛教,强调佛教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无形的观念形态,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实体,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极其丰富的。
(五)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约自1987年以来,我开始集中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经过约15年持续的专攻、研究、撰写,我完成了90多万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于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先后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中华文化优秀著作一等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并列入“中国文库”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出版。全书韩文译本已于2006年出版,日文和英文的翻译正在进行中。
阐发中国哲学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探讨中国宗教理论中国哲学上下数千年,源远流长。历代哲学名家,群星灿烂,学派林立,内涵丰富。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漫长的历史形成、发展过程,蕴藏着精湛的中华智慧,是世界哲学之林中颇具特色、影响深远的一个哲学类型。我一直认为,努力阐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价值,是我们人文学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上世纪80年代,我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撰写了专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我采用问题解析体来写中国哲学史,以问题为纲统领全书,将中国哲学的浩繁史料和诸多头绪,化约为十二个问题: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论、人生理想观、历史观、名实观、知行观、真理观。每个问题编为一章,每章分别由引言、基本内容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内容取材于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的学说,以及玄学、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提要钩玄,客观评述,力争做到博中见约、由约显博的史料梳理与理论提炼。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步伐,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工作需要,作了某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为此,我着重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对中华文化三大传统 (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也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意义。
此外,儒、道、佛三教关系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兴趣所在,我重视三教关系的探索和比较研究,认为这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关键性环节,但是受制于诸多因素,我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成果有限。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传统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经过初步研究,我发现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传统宗教观都有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也体悟到遵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是做好我国宗教工作的关键。宗教不是社会上的孤立现象,也不是文化领域中的绝缘形态,对于宗教必须与影响它的相关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显现其独特的本质与价值。我撰写的宗教与和谐社会、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等关系的小文,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本文摘编自《求是园名家自述》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