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知识的栖居与纸墨间的旷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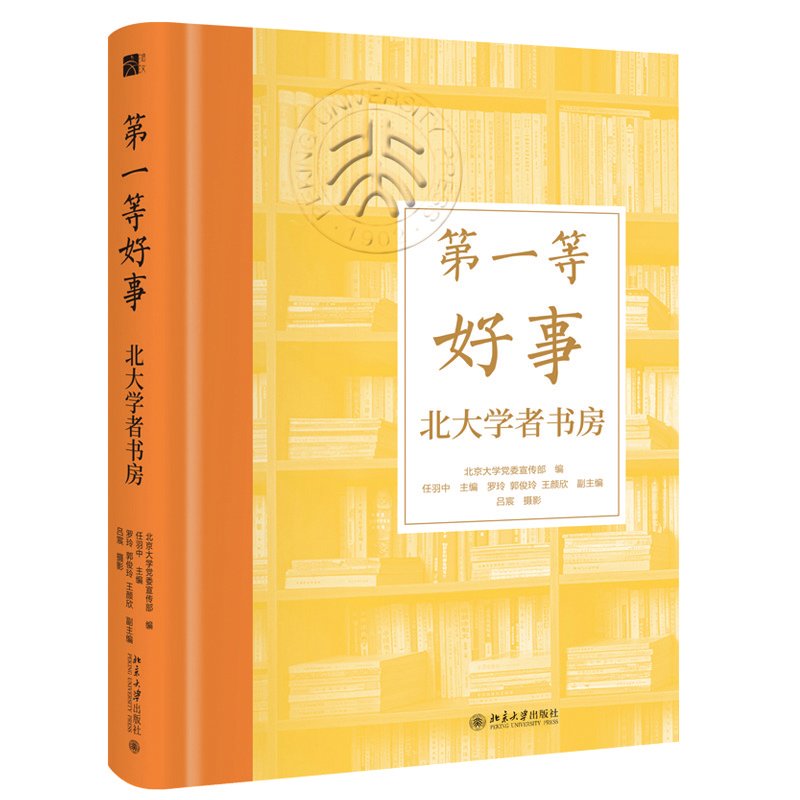
由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著的《第一等好事》(北大学者书房第二辑)书影
未名湖畔,湖光潋滟,塔影婆娑。在这片承载百年文脉的土地上,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思想的跫音交织,构成了北大最深邃的风景。《第一等好事》(北大学者书房第二辑)以“书房”为切口,将镜头对准16位北大各学科领域代表性学者的精神原乡,在纸墨间揭开他们学术常青的密码。治学之道,最重要的无外乎三者:书房、阅读与学者。书房是精神的栖居地,阅读是文明的呼吸声,而学者则是知识的摆渡人。书中,三者交融为一,织就了一幅跨越时空的学术星图。如是,《第一等好事》绝非简单的书斋图录,而是一次深入学者精神世界的思想之旅。
书房:精神的拓扑学
在人工智能席卷一切的当下,“书房”似乎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隐喻:它既是物理空间中最私密的角落,又是思想疆域里最开放的宇宙。书房的四壁既是围栏,亦是桥梁:围栏之内,学者与自我对话;桥梁之外,思想向八方延伸。
拓扑学揭示空间在连续形变中保持的本质属性,书房的精神性亦在于此。无论是堆叠如山的古籍,还是依主题分列的专架,书架的高低错落勾勒出学术视野的起伏,书籍的排列组合映射出思想的经纬。书中,北大学者的书房形态各异:贺桂梅老师的“书墙”如文学史的横截面,从中国古典到西方文学层层叠叠;范晔老师的书柜陈列着西班牙和拉美文学的瑰丽图景,置于其中的侠客摆件与书籍相映成趣,竟无丝毫的违和感;于铁军老师的书房八千册藏书依语言和领域分门别类,宛若一张恢弘的战略地图;贾妍老师的“猫主题书房”似艺术的拼图,将学术的严谨与生活的诗意调和。
物理意义上的书房不过方寸之地,却因书籍的存在成为多重时空的叠加态。打开一本先秦典籍,便踏入诸子争鸣的稷下学宫;翻阅康德手稿的译本,又能与哥尼斯堡的星空对话。书房中的学者站在古今时空的交汇点上,以书籍为棱镜,折射出人类文明的谱系。这种精神漫游的广度,恰是人工智能难以复制的特质。算法可以解析文本的逻辑,却无法体验在故纸堆中偶遇灵光的颤栗,更难以理解书页间留白处潜藏的未尽之意。
数字时代的书房更显现出拓扑学的动态性。如今,电子书与纸质文献共存,云端资料库与实体书架互补,书房早已突破四面墙的桎梏,演变为虚实交织的复杂网络。程美东老师电脑里整齐排列的八百多个文件夹,其中垒叠的中共党史资料文献,清晰展示了百年峥嵘的剖面。苏祺老师的“电子书房”以代码重构古籍,让《永乐大典》在数字世界重生。书房的精神性不在于载体的形式,而在于知识组织的有机性。如同树木通过年轮记录气候变迁,书房通过书籍的聚散映射着学者思想的生长轨迹。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书房便是这语言之家的物化寓所。透过书中这些精心营造的书斋空间,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看到持久的阅读、严谨的治学如何塑造一个人的内在宇宙。
阅读:对抗信息熵增的仪式
在效率至上的时代,“阅读”常被简化为信息攫取的工具。而书中,北大学者却将阅读升华为对抗熵增的庄严仪式。熵增定律揭示宇宙终将走向无序,借热力学熵增的隐喻,我们得以凝视文明对抗精神无序的努力。阅读是这种对抗的微观镜像,即通过构建个人认知秩序抵御信息的熵增。邱泽奇老师为撰写硕士论文手抄千余张卡片,字迹在泛黄的纸页上凝成学术的年轮。程美东老师以“笨功夫”阅读整理浩瀚繁多的史料书籍,在信息洪流中打捞历史的切片。孙明老师早出晚归,查阅抄录巴县档案,奔波持续一月之久,让文字在反复摩挲中垫成学术研究的一块块“砖石”。我们身处的当下,碎片化信息如沙尘暴般席卷认知疆域,短视频将人们的思维切割成闪光的断片,那些伏案抄录的指尖、反复批注书页的笔迹、在故纸堆中逡巡的目光……一个个看似“低效”的笨拙姿态,恰是对快餐式知识生产和消费的无声反抗。
书中暗藏一条关于阅读本质的线索:当今世界,算法推送替代了旧书店的偶然邂逅,电子屏幕侵蚀了纸质书的触觉记忆,我们为何仍需阅读?答案或许藏在一组悖论中:越是便捷的时代,越需要笨拙的坚持;越是确定性的算法,越需要不确定性的探索。阎天老师说:“一本书码起一座城堡,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既可以抵御自身的焦虑,也可以抵御外界的诱惑。”阅读的真正价值不只在于占有知识,更在于通过文字与人类最优秀的头脑共振。范晔老师在《百年孤独》中看到魔幻现实主义的情境投射。邱泽奇老师跟随导师费孝通先生在田间地头找到家国情怀的共鸣。陈平原老师和夏晓虹老师不统计藏书,不务求珍本秘笈,无意炫博好奇,常常在书本流转中体味人情冷暖。书籍于他们而言,不是冰冷的字符,而是情感的寄托、生活的镌刻。
数字时代的阅读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精神生态的预警。当推送机制用“猜你喜欢”驯化思维,当跳转链接将深度思考切分为闪烁的节点,我们不仅失去了宝贵的专注力,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想的活力。北大学者对阅读的坚守,恰似在数字荒原上的一片绿洲。那里允许迷途,鼓励迂回,珍视在字里行间“走失”时偶遇的灵光。或许,阅读的终极意义正在于这种“无目的性”的漫游。那些被笨拙抄写的句子、被反复勾画的段落、在书页间夹藏的批注,最终都化作抵御熵增的堤坝,证明着:在信息泛滥的纪元,仍有灵魂选择以文字的密度对抗着无序与涣散。
学者:在词语的深渊中打捞星光
学术的崇高性常被误解为与世俗的疏离,仿佛学者是栖居云端、不染纤尘的观察者,以冰冷的目光丈量人间。而本书最动人的篇章,恰在于揭示北大学者如何在学术生涯中与书籍相互成全。陈平原老师与夏晓虹老师的“书城”里,典籍从地板蔓至天花板。他们始终保持着“职业读书人”的通达,不为藏书而藏书,只为在文字中照见古今。李彦老师的书架上,世界各地的茶杯与化学模型“并肩而立”,书橱的相框里记录着她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北大学者以笃志的热忱投入知识的汪洋,又在字里行间不断发现自我,升腾起热烈的生命温度。
这种探索的温度,源于北大学者对“人”的深切关怀。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在邱泽奇老师的乡野步履中延续。淘宝村、数字经济、禁毒项目、艾滋病防治项目……在邱泽奇老师的眼中,书房中的孤灯与社会旷野的火把紧紧相连。赵冬梅老师说:历史学者是代表族群探索有关“过去”这一知识领域的人。更重要的是,学者获得知识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要分享。让知识成为照亮现实的炬火,飞跃象牙塔,去往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旷野,才是学术的终极意义。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北大学者在阅读与思考中链接起精神上传承的纽带。于铁军老师的书架上置放着导师袁明老师赠予的两百多本专业书籍,师生间学脉相承跨越时空。易莉老师与学生无私地分享科研心得感悟,出版研究生学术写作指导书《学术写作原来是这样》,照亮了无数年轻学人最初的科研之路。代代北大学人,在写书、赠书、评书、荐书中达成心灵契合,齐力托举学术的薪火。
掩卷而思,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群超凡脱俗的智者,而是一群以学术为志业的普通人——他们也会在挑灯夜战时疲惫,在田野调查中困惑,在学术争论中较真。书卷气与人间烟火,在此交融。北大学者的书房里落满红尘,蕴藏着“不为功名富贵”的洒脱,亦凝聚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书房之外,仍有旷野
杨立华老师在本书序言中感慨:“人工智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跃迁,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阅读形态不可避免会发生改变,但阅读本身会被替代吗?”《第一等好事》最终指向一个书房以外的命题:在数字文明席卷一切的今天,如何守护人类精神的“慢变量”?北大学者给出的答案藏在各自的人生选择中。他们以书房为起点,却从未止步于四壁之内。章永乐老师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待解读的文本,外面是无形的书房。”书房的概念早已突破物理空间的桎梏,演变为流动的精神场域。真正的书房,恰恰存在于对书房的超越之中。
合上此书,耳畔仿佛听见未名湖的水波声与书页的簌簌声交织成曲。在算法统治的喧嚣世界里,北大学者用书房筑起一座座精神的灯塔,提醒我们:阅读仍是人类对现代社会浮躁、惰性、空虚等元素最古老又最有效的抵抗。或许这正是“第一等好事”的真谛:在书页翻动间,我们始终相信,有些火光永不熄灭。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