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光影】
嗅着花香的蜜蜂
——读汪曾祺《在西南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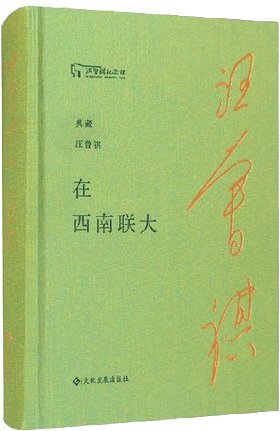
第一次知道汪曾祺是在初中。那节语文课有点喧闹,现在回想起来却十分令人怀念。王涣老师讲汪曾祺《端午的鸭蛋》,我一听题目,便觉不俗,有味道,尤其是描写高邮鸭蛋吃法的内容,至今还时时满溢在嘴角。
汪老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老师讲到这里时,我的大脑不禁闪过一幅生生动动的画面:热闹非凡的端午节,系着红绿色彩绳的手腕白胖白胖的,他正拿着一个精挑细选的淡青壳鸭蛋和兄弟姐妹们围坐在庭院前的小板凳上。他左手拿着鸭蛋,右手拿着一根竹筷,滚圆滚圆的脑袋在晌午的太阳下照得白亮白亮的,像明镜似的反光呢!他微抿着嘴角,熟练地将筷子对准鸭蛋的“空头”,敲了几下,只听“咔嚓”一声,鸭蛋顶部破出了个小洞,他调皮地微笑着,用筷子一头扎下去,吱的一声,红油冒出来了。
那堂语文课,我仿佛跟随汪曾祺回到了他的老家,回到了江苏高邮,也回到了他的童年。自那以后,我竟对“江苏高邮”这个地名产生了莫名的好感,闲暇时刻总是会想象那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我知道“江苏”属于南方,是水乡,也是鱼米之乡。可那里到底是和印象中的,和我凭借有限学识拼凑出来的“高邮”不一样的地方,否则怎么会让我如此魂牵梦萦?我想起“高邮”,有时是在做完功课后,有时是在即将入睡前,有时是在下着秋雨的窗前,有时是在堆满积雪的林荫道……那时的“江苏高邮”是我向往的地方,亦是我憧憬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
再次研读汪曾祺的作品是在高考后的夏天。这本《在西南联大》让我走进汪老的世界,来到战火纷飞的三四十年代。那时粮食短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很多百姓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可也是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什么都“不缺”。物质的匮乏阻挡不了他们追求知识的脚步,也正是这样,他们的精神世界充盈和富足,他们的心里装着的不仅是各自的小家,还有大家,还有中国。他们跋山涉水,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来到了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在这里,他们开启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求职生涯。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他们的求知欲跨越物质的鸿沟,拼命联结成知识的“圆圈”。西南联大的生活,在汪老笔下如此生动有趣。
逛书店,到南屏大戏院看电影,逛裱画店,在裱画店欣赏吴忠荩老先生写的极其流利但用笔扁如竹篾的行书四扇屏……逛茶叶店,品味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还曾在名为“凤翥”“龙翔”的两条丁字形的小小的横竖街闲看,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头卸货、装货、喝酒、吃饭的地方,我好像都随汪老一起去了一趟似的。
联大里的老师,像朱自清、金岳霖、沈从文等,都在汪老的描述下十分生动有趣,有穿着破拖鞋的,有一件破袄穿了十几年都没舍得扔的。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也是联大老师们简朴节约生活的写照。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汪老和联大的其他同学一起捉豆壳虫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了一点花椒盐,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我们也爆了一盘,闭着眼睛尝了尝,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多得很,一会儿就能捉一大瓶。”
读过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书,没有一本能像汪老描述得这样纯真快乐。更可敬的是,他们心中有着比这课外趣味更重要的事,那便是救国救民,凭借一腔热血,持之以恒的毅力与丰富的学识拯救民族,建设国家。很多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其中不乏在后来获得“两弹一星”荣誉的科学家。他们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作为新一代大学生,拥有如此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再为衣食发愁,又有何理由不努力呢?西南联大,好比尘埃中开出的一朵花,微弱而倔强,《在西南联大》就是嗅着花香的蜜蜂,把花粉播撒到了祖国大江南北。先生们的足迹,也已深深扎根于长城内外。我们要做的,便是追寻着他们的背影,放慢脚步,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做对国家、社会、人民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