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的叙事策略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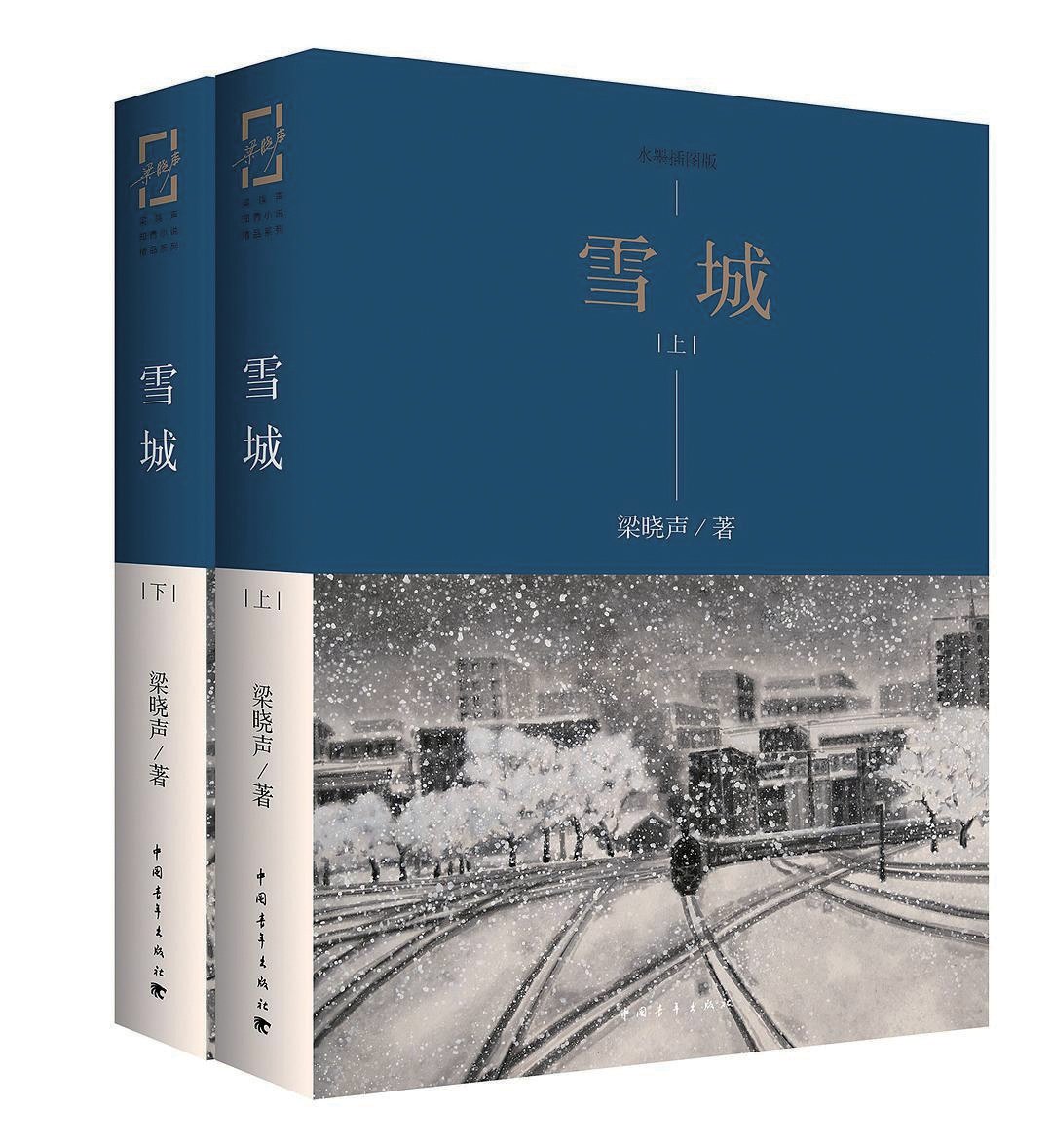
摘要:梁晓声以独特的北大荒知青经历创作了独特的知青小说,《雪城》是梁晓声知青文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不同于前两部作品描写知青岁月,《雪城》将目光投向知青返城后的生活,同时文本也具有梁晓声特色的叙事策略。从叙事时序来看,《雪城》整体上采用连贯叙事描写主要人物返城生活,对于知青时期的记忆采用闪回的逆时序创作,形成波澜起伏的情节变化;从叙事结构来看,采用单向的线性情节模型;从叙事视角来看,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一切。
关键词:《雪城》;叙事学;时序;结构;视角
梁晓声是文坛上少有的跨世纪持续创作的作家,从上世纪的知青书写,到新世纪的平民书写,梁晓声的创作也在跟随时代而变化。从《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到《雪城》是梁晓声80年代的知青题材创作的巅峰,他的文字一反诉苦意味,转向抒发青春的崇高理想和勇敢无畏的知青精神。《雪城》可以称作梁晓声知青系列的转型之作,《雪城》创作于1986年至1988年,随着80年代后期“知青热”逐渐退却,大返城年代到来,梁晓声将目光转向知青返城后的生活。《雪城》作为梁晓声经典知青题材的代表作品,独特的知青视角在叙事模式方面呈现出别样的特色,本文将从叙事时序、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时序:连贯叙事与逆时序相结合“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969年,由法国叙事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首次提出,也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正式形成。早期以热奈特、罗兰·巴特、托多洛夫等为主要代表的经典叙事学对国内外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热奈特所讲的时序包括故事时序和叙事时序,故事时序指被讲述的故事的自然时间顺序。叙述者常根据自己的审美意图,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有意打乱故事的自然时间顺序,重新剪辑、排列组合,这就衍生出叙事时序。故事时序等同于叙事时序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具体文本中二者常是不等同的,常常存在着提前或置后的情况,即我们常说的时间倒错现象。由此构成节奏、形成张力,进而诠释作者的美学思想。”
违背故事顺序发展的时序称之为逆时序,总体上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呈现单一清晰的线性运动,在整体直线叙事的基础上采用连贯叙事,在情节之中穿插倒叙,对一些时间回忆与追溯采用闪回的形式。《雪城》主要展现的是知青大返城后的生活,小说从1979年12月26日开始叙述,在A市火车站,一辆满载北大荒返城知青的火车驶入,从环境描写开始,引出由姚玉慧为代表的返城知青群体,整体按返城后的时间顺序,以人物为章节划分依据,叙述每个主要人物的返城生活,但知青时期的生活会以倒叙回忆的方式展现,从返城后的种种磨难、挫折、无助与知青时期的热血、激情形成对比,通过闪回记忆将知青生活展现出来,例如姚玉慧在卧室读到《简·爱》时,不由得回忆起作为营教导员在兵团的生活,回忆起和营长的种种过往:“这种静真美好啊!她努力回忆,回忆起在到北大荒后的十年,不,十一年中,有过享受这种美好的时刻。不惜时间流逝,不被周围的任何事物干扰。像是在梦里,又知自己不是在做梦。可以静静地去想,可以去想与一位教导员毫无关系的事,可以只想与女人相关的事,这简直是一种幸福。”由此开始展开与营长的故事和知青生活,而在一个记忆片段的结束后又会继续承接原有的返城生活叙事,叙事时序的结合使用造成了文本时序的不连续性,也因此使叙事更加波澜起伏。
二、结构:线性情节模式“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可分为性格模式、因果模式和情节模式,而情节模式大多数以情节为结构中心。”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即呈现出传统的线性情节模式,《雪城》的线性情节与人物紧密相连,“一般来说,事件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物性格成长的过程,因此在情节模式中,人物与事件是相辅相成的。情节模式的小说由于始终关注人物的命运,并尽可能提供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经验和能够唤起中毒者情感波澜的细节,并以此使读者产生共鸣。”
在叙事结构方面,《雪城》是以“时间”为主轴,以“事件”为轴心,以“空间”为延展,“时间”与“事件”相结合的线性结构模式。从时间轴来看,《雪城》的故事发生在1979年12月26日,故事以姚玉慧、徐淑芳、严晓东、刘大文等人的返城生活为主,但其中也穿插了知青时期的记忆。从空间轴来看,小说以姚玉慧、徐淑芳、严晓东、刘大文等人的返城生活为主,而每个空间则以“事件”为中心。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线性结构模式既让小说结构上更具有弹性和张力,同时也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从纵向来看,《雪城》上、下两部有着明显的线性时间轨迹,故事的开端时间是1979年12月26日,从载有二十余万返城知青起笔,将姚玉慧、徐淑芳、严晓东、刘大文等人的返城生活以章节形式展开,每一章叙述一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但故事中会出现与之有关联的次要人物,这也就成为下一章的引子,环环相扣。故事情节并不因为线性叙事而平淡无奇,相反在连贯叙事的基础上穿插闪回记忆,既能保证小说整体的完整性,也能拓展情节的时空,让知青的人物更加立体,同时也加深了小说的主题意蕴。例如小说第一章通过寒冬中的火车站营造一种迷茫焦灼的气氛,在章末引出市长女儿姚玉慧返城归家的场面,第二章紧接描绘市长的女儿,通过和家人的相处介绍基本情况,并采用倒叙的回忆展现北大荒的经历,从姚玉慧的视角引出徐淑芳的故事。而后也引出刘大文、严晓东等人,这些故事情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形成了链式线条,同时指向重现知青一代的历史命运,以及知青返城后待业的迷茫与世俗生活的苦难主题。
三、视角: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学理论中,第三人称中的“叙事者站在故事的虚构世界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讲述小说中的人和事。其标志性叙事者用第三人称代词‘他’指称作品中的人物。第三人称自由客观,便于广泛地反映社会与生活。”第三人称以无所不知的视角,从所有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自由灵活,亦可称作“上帝的眼睛”《雪城》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者站在局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一切,超越时空距离,将每个知青的“前世今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叙述,冷静直观地反映北大荒时期的兵团生活以及返城后格格不入的城市生活,作者站在人物背后,纵观全局,俯瞰一切。例如《雪城》中采用“上帝的眼睛”,叙述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雪城》是一部知青题材的作品,梁晓声用全知视角讲述了这一代人的故事。在传统文学中,视角与叙述视角是相对的,叙述者站在叙述角度观察人物和故事,作者以“上帝身份”叙述故事,而全知视角则是在叙述角度之外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超越了时空,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没有拼力搏击的快感,只有无始无终的忍耐,没有堪为之献身的崇高,只有生活无着的烦恼,没有游子还乡的欣慰,只有新的失落和幻灭。梁晓声的笔,第一次这么严酷,他把作品的主人公们一次又一次地打落水中,不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不给他们以片刻的安宁,公开的招考背面是阴暗的骗局,辉煌的歌声未尽却衍化成啼血的哀音,悲壮的游行竟引发出地面坍塌的惨剧。”当作者站在上帝视角“摆布”这些返城知青的生活时,人物也只能被迫地在梁晓声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地与世俗作斗争,全知视角让人物命运走向变得有迹可循,刘大文为了爱情而放弃“金嗓子”,在短暂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之时,却遭遇妻子的意外离世,从此一蹶不振,戏剧性的走向背后更是现实的映照,从细节处总能发现刘大文身上背负着梁晓声的理想主义,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守护,甚至可以放弃一切,只有俯视这一切才能发现性格、环境对刘大文一家命运的影响。
《雪城》是一部现实且悲壮的后知青赞歌,既是对现实的写照,也是对知青理想顽强地追求,通过连贯叙事与逆时序结合的叙事时序、线性情节模式的叙事结构以及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事策略,将二十万知青大返城的生活浓缩在几个人主人公身上,通过叙事让文本变得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1]王桂梅.由热奈特的叙事时间理论看《边城》的叙事艺术[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3(1):3.
[2]梁晓声编.雪城[M].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3]寇荣波.梁晓声知青小说创作模式论[D].陕西师范大学,2013.
[4]孟繁华.叙事的艺术[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5]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6]白春香.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5.
[7]张志忠.未曾衰竭的青春——读《雪城》兼论梁晓声[J].当代作家评论,1987(3):5.
[8]武孟超.梁晓声北大荒知青小说论[D].牡丹江师范学院,2017.
[9]吕洁宇.无法逃离的时代记忆[D].西南大学,2012.
[10]段晓丹.梁晓声小说创作论[D].河北师范大学,2009.
(本报文艺评论员,文学院2020级汉文一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