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师范大学 - 《河南师大报》
浮世南京
作者:◆历史文化学院 王子月
2018-07-09
浏览(93)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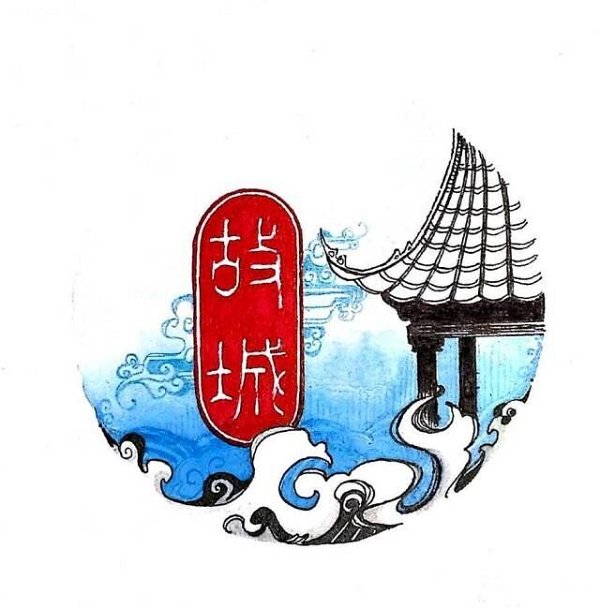

五月一日的午后,我再一次坐在了玄武湖边,闷热的气息蒸腾着从镂空的木板下传来,还有水里莫名的味道。远处的古城墙是另一半玄武湖,离我很远,昨天我在那里坐。天有点阴,一副山雨欲来的模样,湖里的小鱼不住地跃出水面,对岸的城墙也显得绰约,也许真的要下雨了。“嗳,走吧。要下雨了。”同伴拍了拍我,我们缓缓向背后的南京火车站走去,谁也没有因为将来的大雨乱了脚步,谁也没说对这个城市多么不舍,就这样慢慢走了。乘电梯到二楼候车厅,踏入候车厅的那一瞬,雨下来了,溅起尘土,慌乱的人群拥挤着,鼻腔最后涌入的便是水汽和泥土含混不清的味道。我是不能讲对这个城市的眷恋的,讲了好像是对家乡的背叛一样。毛姆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我觉得机缘把我抛掷在了家乡,即是最好的安排,而对别的城市,我依然会生出眷恋之情,眷恋那里的秣陵路,眷恋那里的糖芋苗,眷恋满城的梧桐树。这真的是一种浪漫而又纠结的情绪,正如我也不知道所谓的“家乡”坐落在哪里。
我最后看了一眼它大雨如注的模样,来不及细细品味它,就要离开了。说起来,不过是一场平常无奇的旅行,短短三天,一切都显得来不及。时隔数日,其中的滋味才慢慢咂摸出来,就像傍晚的老门东,那时眼里不过是它的繁华景,如今却想起余晖下的马头墙,白墙黛瓦,盛着夜幕下的光怪景象,闷燥的空气黏在皮肤上,不小心被前面姑娘的白裙晃了眼,虚幻中夹杂着莫名的快乐。
夜幕升腾起食物的香气,同伴对南京的烤鸭肠爱得深沉,丝毫不惧那等待的队伍已经从街头排到巷尾,不过看他餍足的模样,情愿又去帮他排了一次队。糖芋苗和赤豆元宵的甜糯,让我平添出一种南京人真幸福的感觉,夜里来一碗赤豆元宵,热热得直钻进人的心里,再多的疲惫也该烟消云散了,赤豆元宵就像是给这忙碌的一天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一如它小小的模样。当我们无意间转出老门东时,发现了一家特别的柴火馄饨铺,柴火馄饨四个大字就像是烧过的柴火棍子信手写在木板上的,有种不羁的意气,与一巷之外的老门东格格不入,却又觉得南京老城本该这个样子。经营铺子的是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六块钱一碗的馄饨格外实惠了,清亮的汤汁,细碎的绿意漂浮其上,吃起来竟真的有淡淡的烟熏味道,意外的满足爬上心头。
可能我最喜欢的就是南京的夜色,白日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不去景区的话,可能根本感觉不出来南京和郑州有什么不同,夜里就不一样了。当一切都陷入黑暗和霓虹灯时,一个城市才能显示出它的不同寻常来。晚上倚在秦淮河的护栏上,累到有些脱力,晃晃悠悠的河水随着波光,像是所有情绪都随之流走了。我们神经质地把杜牧的《泊秦淮》吟了一遍又一遍,拼尽全力来想象那时的秦淮河是何模样,是否如眼前,游人如织,游船也如织。不过,这里的游船可能是最煞风景的存在了,模样千篇一律,没有丝毫流传明清的情致,穿行得也快,不像是夜游秦淮,倒像是完成一项任务似的越快越好,若是在明清,才子手里的酒,怕是要洒了一整个前襟,只剩下狼狈,哪还能得什么风流倜傥。不过这船的名字也算是用了心的,“玩月”、“明德”,有对面江南贡院里才子笔墨的意思。不管时代怎么变了,秦淮河始终就是这模样,该绮丽绮丽,该静谧静谧,当年流过的脂水,还在慢慢发酵,吸引这一代又一代的游人。
南京的梧桐树茂然如盖,显示出春天青绿温软的模样,最怕是春归了秣陵路,却是归期已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