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 - 《吉首大学报》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理性
作者:易小明
2018-03-20
浏览(83)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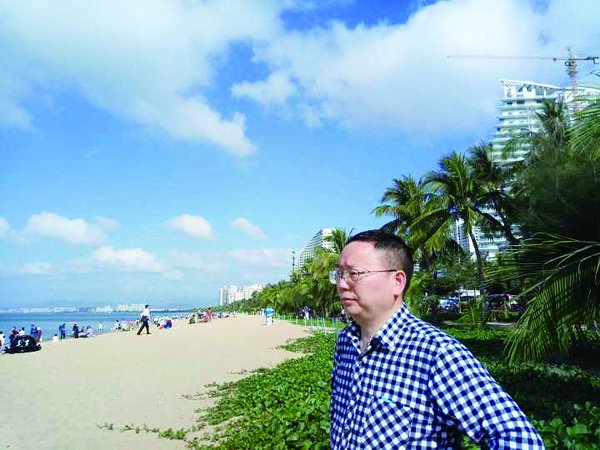
图为易小明教授
今天的网络,无数国人对于同一事件的相互撕逼已是常态,针对此状,人们都在努力呼唤共识,而我则试图努力呼唤理性。因为在我看来,若要共“识“,先得共”理”,这不仅是一个“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更是因为,理性是共识生成的唯一正途———并且,它不仅是共识生成的必然途径,也是检验共识、发展共识的必然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而理性,正是抓住事物本质的“抓手”。
对于理性,哲学史上有多种解释。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以区别于感觉、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有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理性指在经验中无法达到的知识的完备性和无条件性,即对世界、灵魂和上帝的认识能力。它作为认识的最高阶段,不仅要认识自在之物本身,而且要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的无限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概念也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上阐释的,它重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与飞跃。其实,理性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不仅包括人们应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也包括人们对行为进行选择、批判、辩护的能力。
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发展过程,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甚至根本性特征。由于理性不仅要为“自然立法”,还要为“自由立法”,所以理性担当着社会建构的伟大使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民主与法制,既是理性引领的结果,又得不断受到理性的检验。而一个社会如果广泛缺乏理性、或者理性的价值普遍受到贬斥,那么社会上流行的一定是人们泛滥的情感、任性的意志,是少数人失去制约的权力,是多数人遭受奴役的命运,这样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异化的社会、非人的社会,因为人的本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的持存。
保持理性,必然要对社会上的任性和妄为说不,因此,对诸多事物进行自觉批判是理性能力的必然表现,当然也是主体性丰富、发展、成熟的现实表现;反过来,主体也正是在对自然事物、对社会事象的持续批判过程中不断进步和完善的。正基于此,康德提出,一切事物都需要反思,包括理性自身都必须遭受批判,正是在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人类的思维才达到如此的高度和自觉。所以康德呼吁:鼓起你的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叫吧!
相较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重情”特征,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不断生成和造就了我们的情感思维特别发达而理性思维相对不足的状态。人们说话办事,从“合情性”角度考虑问题较多,而从合“合理性”角度考虑问题较少。这一方面使我们沉浸在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自得其乐,另一方面却也容易导致我们背离社会原则、违犯自然规律,从而导致人们情感化、情绪化、人情化、主观化的错误不断出现。由于“情感灵活性”有余而“理性规则性”不足,整个社会就缺乏一个运行基准,这样的社会,往往情大于理、权大于法,普遍的不公平现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它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更不利于制度的充分完善,因为正义是社会的客观基础,而理性则是正义的主体基石。
由于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内在差异及其总体发展进程的不平衡,就导致中西方理性发展之时代性“错位”,当今天的国人努力发展补充我们的理性时,西方却又开始了对理性的广泛批判,正如有的人还没有饱饭吃,有的人却想减肥了。于是就有人提出,我们还发展理性?这不是捡拾别人的弊屐吗?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西方的理性批判并不是对理性本身的否弃,而是对于过度理性的批判,不是对理性之“质”的否定,而是对理性之“量”的反思。他们认为,把理性当作唯一准则的理性主义,视理性为人的唯一本质,从而忽视了人之应有的非理性价值。正确的理性教育,应当在强调理性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感性的必要性,因为感性与理性是相互依存的,理性的生成离不开感性的积累,而感性的出彩也离不开理性的指导。而从人的心理过程来讲,它作为知、情、意的统一体,人的活动,若离开了情与意的参与,单纯的知是独木难支的。所以,对过度理性的批判并不是要走向否定理性的极端,而是要使理性的表现恰到好处。
但是,中国的情况又有重大不同,我们不是理性发展已经过头而是理性发展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国情来选择不同的发展策略,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或囫囵吞枣。如果不顾“病情”而照搬西方的“药方”,就必然使我们刚刚起步的理性教育中途夭折,“刚开头又煞了尾”,必然回到情绪渲泄、意气用事的任性沼泽。所以,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理性,而不是如何节制理性,因为拥有理性是雪中送炭,拥有恰当的理性才是锦上添花,要想锦上添花必先雪中送炭。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而法治通行的基础就是理性的广泛存在,因此,理性构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有首先拥有它,我们的生命才有依恃的力量,我们也才能走向人生的灿烂花期。
生命的高贵就在于生命的自由,而自由虽也内含着观念的任性与冲动,但现实的自由总是基于对必然规律的遵循、基于对道德法律的遵守,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性不仅是主体成功的关键秘密,它更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
理性如此重要,于是我们就不得不给自己提出一个必要的常规性反思要求:我们如此思考、言说和行动,理性吗?
(易小明,1965年生,湖南省龙山县人,土家族。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留德、留英学者。主持、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30项;著有《社会差异研究》等著作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8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获省优秀社科课题成果一等奖1项,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首届“百位社科人才”培养对象,湖南省省级学术带头人。2008年聘为中南大学升华学者特聘教授,2012年聘为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2017年聘为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系中国价值哲学学会、中国民族伦理学会、湖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伦理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