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科技大学 - 《苏州科技大学报》
辛亥革命苏州和平光复的伟大意义
作者:□人文学院教授高钟
2016-11-30
浏览(787)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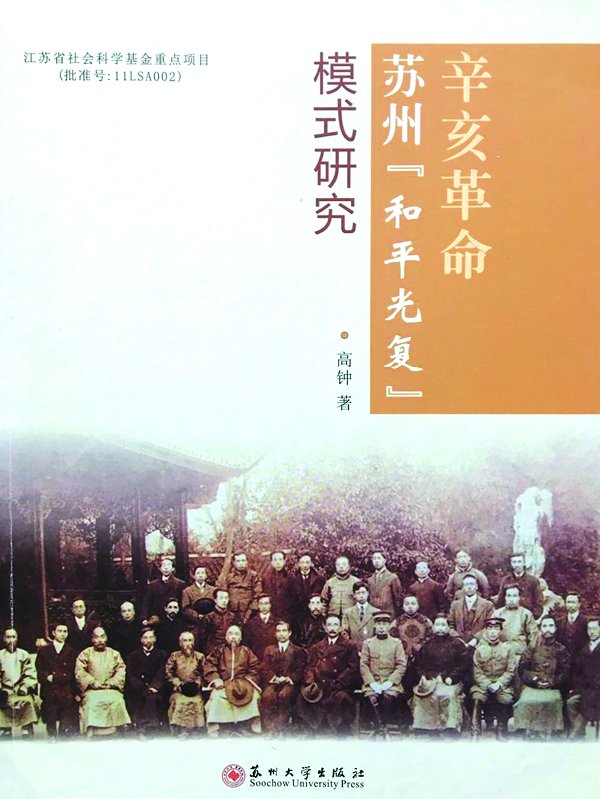
辛亥革命是一场结束了中国三千年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改变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实存在着两种革命模式,即武昌首义暴力革命与苏州和平光复的非暴力革命;二个动员口号:武昌首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与苏州和平光复的“满汉一体,五族共和”;两种统一战线模式:武昌首义的下层官兵推动仓促联合与苏州和平光复的上层官员士绅主动结合。这二种不同的模式决定了辛亥革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阶段,即1911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武昌首义的暴力革命模式为主导,湖南、江西、山西、陕西、云南等均是以此模式为仿效;11月4日苏州和平光复后,其后各省基本上是按苏州和平光复的非暴力形式、满汉一体的口号,高层官员与地方士绅主动结合后倒戈。所以,辛亥革命其实是首义于武昌,收功在江南,转折点在苏州,程德全就是推动这一转折的主推手之一。
苏州的和平光复对于辛亥革命有着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什么105年以来,对于辛亥革命人们只知道武昌首义,而很少人知道苏州和平光复呢?而且相当一个时期,对之都加以“假革命”、“投机革命”的恶谥,这不仅是意识形态史学造成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对于什么革命,革命是否就是暴动,革命是否就一定要暴力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没有弄清楚。“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主宰了人们的头脑与判别能力。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早已讲过,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可以用暴力,也可以用非暴力。只要是解放生产力就是革命。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改革毫无疑义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暴力革命其实往往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任何革命都会伴生着暴力失控,从而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严重的破坏,这是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本质相违背的。正是看到了暴力革命的这种暴力失控的弊端,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王歧山同志近几年要求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让大家看到暴力革命伴生的暴力失控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苏州和平光复模式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在动员口号上纠正了武昌首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一个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口号,而代之以“满汉一体、五族共和”这样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口号。前一个口号是不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版图完整的,是极易引起民族仇杀、民族分裂与国家分裂的。在苏州和平光复之前,武昌、太原、西安都发生过误杀或滥生满族平民与解除武装的官兵的现象,太原、西安旗营因此而发生拼死的抵抗,双方死亡惨重。在苏州和平光复之前,江苏镇江旗营也是准备拼死抵抗的。但苏州和平光复高扬的是“满汉一体,共享太平”的旗帜,特别提出了对满人给予国民待遇。由此,镇江旗营放弃了抵抗,交出了武器,这不但使镇江一营免除了战火,更重要的是为全国的旗营做出了典范,杭州、福州、广州等地旗营最后都与镇江旗营一样,主动缴械,得到礼遇。而这个口号也推动了清廷中央的退位,清帝退位诏书由苏州和平光复的推手之一———张謇最后润笔而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五族共和,满族与其他各族一样有国民待遇,其王室成员同样如此,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们就不会如困兽一样拼死相斗,而采取主动的逊位,以获得更好的优待。
过去指责苏州和平光复是程德全、张謇等人投机革命,其实是没有看到他们由“君主立宪”走向“共和立宪”的内在合理性与逻辑性。程德全与张謇在辛亥革命前都是著名的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这就是武昌革命初起时,程德全、张謇还向清廷中央上疏四次,要求清廷中央尽快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成立“责任内阁”的原因所在。但昏庸的清廷中央对此四疏均不报答。他们对清廷失望,明白想依靠清廷中央实现“君主立宪”是不可能的了。这条路被清廷中央堵死了。而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其根本点在于“立宪”,即按照宪法来实行国家行政。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有了个“虚君”,即不负行政责任的皇帝,后者则没有,而是以民选的总统来担任国家元首。那么,既然清廷中央拒绝了当“虚君”,建责任内阁的自救之路,大多数的人民又都赞同“共和立宪”,程德全、张謇等立宪派转向共和立宪就顺理成章了。这个转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理性选择,是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性与合理性的。指责他们投机革命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们最后都始终坚持了共和立宪的主张,极力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与张勋复辟。
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因为先后发生了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并将这个失败归之于苏州和平光复模式影响下,革命不彻底、没有动员人民大众,旧官僚投机,依然盘据在新政权之中,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任何革命都有二个阶段,首先是政权的易手阶段,其次是新政权的制度建设阶段。辛亥革命在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的影响下,以不到百天的时间内完成政权的易手,其革命成本之低是世界罕见的,其胜利应当是值得肯定。而要在一个小农经济主体,流民遍地的社会、三千年帝制包袱、文化精华与糟粕未得厘清重建的情况下,立马建设成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新型国家体制是需要时间的,更何况还有俄、日两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在旁极力干涉中国内政,煽动各种形式的叛乱与分裂,从而使辛亥革命后的现代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建设工作一波三折,历尽艰难,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理论上的确定与实际上的开展,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意义也就在于此。苏州和平光复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