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业大学 - 《湖南农业大学报》
当用唯物史观映照历史小说
———读《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1] 一书评说
作者:离退休处 汤孝林
2017-03-25
浏览(121)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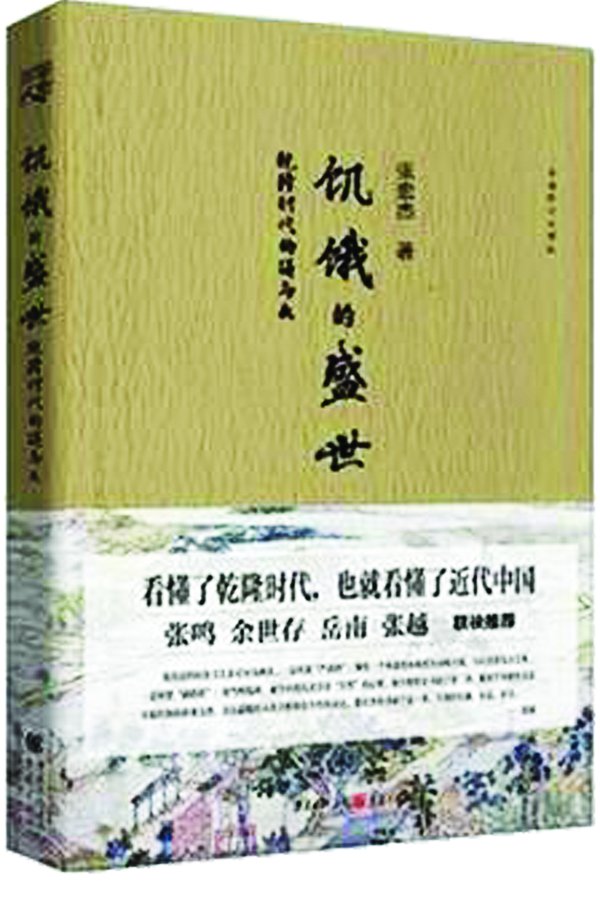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本人年逾八旬,欣逢盛世,喜欢阅读书刊、争取进步,阅读对养生有利,更增读书兴趣。近期,得学友推荐,阅读《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有一些心得,写出这篇评说,请读者朋友们指正。
这本书是2016年的畅销书,其中心内容是写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阅读后,我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是,有学术背景把握,世界视野广阔,把乾隆王朝放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美等资本主义列强横向对比,显示出历史沧桑感;作者有扎实的历史学根底,材料翔实,论说精当;既写乾隆作为帝王的施政风格和性格,又在君臣关系、夫妻关系中表现出常人的人性,文思细腻,文笔酣畅,是值得一读的历史小说。
读者与作者平视,砥砺前行,敞开心怀,该书有上述许多优点,但用唯物史观来映照又可以看出一些缺失和问题。
首先,著者的主题《饥饿的盛世》值得商榷。
历史表明“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英国等西方列强通过产业革命使社会蓬勃兴起,而所谓“千古一帝”的乾隆,却逆人类文明主流而动,闭关锁国,一心想保持世袭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将臣民牢牢地“关在封建专制的牢笼里”,不思改革,导致落后挨打,埋下许多隐患,并使乾隆王朝之后的清王朝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令人叹息和警醒!
当然,乾隆王朝的饥饿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构成该盛世的主要特征,也不是造成人们苦难和盛世随后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何况著作大篇幅地述说乾隆王朝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不是写其社会的饥饿。
通观全书,本人认为,应当把书名《饥饿的盛世》改写为“不识时务的盛世”。或者如该著作序言中所说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盛世”。这样既抓住了中心,又提升了该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次,著作的内容有重要缺失。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2]中有如下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该论断提供了理解社会形态之门的钥匙,也是映照着《饥饿的盛世》这部历史小说结构上缺失的指南针。它启示我们,社会形态分为三个层次(或基本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本要素构成社会有机体,它们的互相矛盾,促进社会复杂的变革发展。
《乾隆的盛世》大量篇幅述说乾隆王朝的上层建筑,包括王朝统治政策策略、措施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缺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缺少经济基础的描述。
书中“盛世之巅”一章,有“以民为本”这一节。这一节,与描写王朝的经济基础有密切关系。可惜,这一节的写作立场和写作角度没有把握好。应当说,适当描写乾隆与其他皇帝有区别、有特色,是可以的。但把封建皇帝描写为“爱民如子”,把王朝各项政策措施,包括许多安民,辅民,发展生产,有利于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措施,概括为“以民为本”,这就有些南辕北辙了。如果把乾隆王朝各项措施都肯定为“以民为本”,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的“人权”、“人道”措施,与我们社会主义的“以民为本”有何区别呢?我建议,把“以民为本”这一篇的标题取消,把其内容合并到论述乾隆王朝的经济基础的磨难与争斗中去,搜集更加多的历史资料,用大手笔增写一章或两章,基本内容是写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再次是个别理论观点的失误和个别场景中的失态。
书中着重引述黑格尔对待中国道德观念和中国历史的见解。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在黑格尔那里,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都被赶出了他的视野。作者却带着欣赏的态度来转述黑格尔的见解,对黑格尔的错误观点未作任何反驳,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作者接着写道:“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道”。在此处,作者评论道:“黑格尔的思考不缺乏理性的因素。”作者有意肯定黑格尔的观点,这是值得讨论的。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理性正是它自己,它自身的思维就是直接的实在”。黑格尔批评了感觉论,他认为真的使事物被认识的是观念,是“自我”。因此,黑格尔“理性”的内涵是唯心观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阐明:“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物质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改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很明显,黑格尔把道德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作根据,来解释封建王朝“重复庄严的毁灭”,并认为中国这个国家“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是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表明,在特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中,政权、法律、政策等与道德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结合。当前,中国的治国理政战略,是“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即“硬的一手”与“软的一手”相结合,从而取得了政通人和的大好局势。以反腐来说,正是“硬的一手”与“软的一手”相结合,才取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功效。
综上所述,笔者的主要感悟是:历史小说应当尽量反映一定社会的大结构,不能顾此失彼;应当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映照历史和现实生活。
注:
[1]《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张宏杰著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