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报》
实践知性与康德式动机论
作者: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姚文丽整理撰写
2015-03-18
浏览(74)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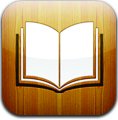
哲学论坛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颜青山做客山东大学分析哲学论坛,做了题为“实践知性与康德动机论”的报告。山东大学哲社学院逻辑学专业荣立武副教授担任主持人。本次报告围绕一般知性的类型和结构、实践知性的存在性与结构、构成实践知性的必要条件、基于实践知性的康德式动机论以及“实践知性与控制理性”展开。
颜青山教授认为本次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在新的哲学背景下回答康德的问题:纯粹理性何以能够是实践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看作自由意志论者面对决定论的挑战之一:自由意志如何能够原因性地决定一个外部的行动?即,自由意志需要因果决定性,但它如何可以同这种决定性连接起来发挥作用?颜青山教授从实践知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般知性的类型和结构首先,颜青山教授从一般知性的角度区分理解的两种理解状态:尝试理解(U1)和完全理解(U2)并描述性的考察它们之间转换关系。然后通过思想实验论证存在相应的实践知性状态:pU1和pU2,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大体类似一般知性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转换。
颜青山教授指出,当我们理解某一事物时,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将被理解的事物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例如,我们先前已经熟悉的某物,即“理解为他物”。但因为这种说明性理解方式涉及了“先前”的某物,它在逻辑上就可能会导致无穷后退,因为我们先前理解的某物,在我们理解它时又可以理解为更先前的某物,如此下去便会无穷。因此,必定存在一种更原初的理解方式,即将某物“理解为自身”。如果从逻辑完备性的角度考虑的话,就必定还存在一种将某物“理解为无物”的状态。
事实上,上述三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在我们理解某物的全过程中。颜青山教授将上述三种情况分为:尝试理解(pU1):将一个行动理解为先前熟悉的行动;完全理解(pU2):将一个行动理解为该行动本身;不理解(pU0):将一个行动理解为无任何行动;习化(pU00):从尝试理解到完全理解的训练过程的特征表述。如果将“尝试理解”和“完全理解”看作两种不同的理解状态,那么,从已有的认知科学证据来看,它们对应于认知双歧任务或双歧过程理论中的两种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尝试理解和完全理解表现在技巧的学习和完全掌握之中。
颜青山教授强调的是,对上述两种理解状态的划分貌似存在反例。在对如符号、语词等表征物的理解中,不管我们处于U1还是U2中,似乎都处于将表征物理解为他物的状态。对表征物或事物关系的完全理解在后面我们对Libet神经生物学实验的重新说明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实践知性的存在性与结构颜青山教授讲到实践知性问题时讲到一个案例:全感知植物人是从来没有过动作或行动经验,也不曾产生过任何行动动机,因此,当他们理解我们的行动时,就不可能从动机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行动。但是,由于他们的感觉能力健全,因此一般知性行为是健全的,他们对我们行动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一般理解的水平。由于全感知植物人具有健全的感觉,他们凭借一般知性能力就能够理解到他人的疼痛和感受。很显然,在此情形下,他们应该能够像我们一样形成同情。那么,他们是否可以由此形成愿望呢?
可以设想,当大风吹刮起风沙迎面扑来时,他们会感到疼痛和难受,而当风停止时,他们的难受不再持续。如果某一个时刻其中一人恰好处在背风处,却看到他的同伴处于风口上忍受风沙扑面,他应该能够产生一个希望风沙停止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犹如我们在看到朋友经受痛苦而又无能为力时希望奇迹出现以中止其痛苦时所产生的善良愿望一样。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人无法产生任何去主动帮助同伴的动机,更不可能付诸行动。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也没有动作的能力。由于“帮助你的同伴”这样的命令或实践理由得到实施必须由一个行动来完成,而全感知植物人没有这样的经验和能力,他们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帮助”这种行动的含义,因此,这样的人不可能理解这样的命令或实践理由。
如果将全感知植物人上述反应同我们健全人进行比较,我们不但能够从动机和意图的角度理解他人的行动,我们也能够因为同情而产生帮助他人的善良愿望,而不仅仅是乞求外在奇迹出现的那种愿望。同样地,我们也能够理解“帮助你的同伴”这样的实践命令和理由,即使我们不去完成这样的行动。
相较于全感知植物人所缺乏而我们所具备的这种理解行动、由同情产生的行动和理解实践理由的能力,就是一种实践知性能力。这个思想实验显示了实践知性的存在性。实践知性这一类型的特征完全可以类比一般知性行为。
实践知性的必要条件与康德式动机论颜青山教授认为,全部实践知性的核心问题是动机的产生或形成,进而是对动机的理解问题。实践知性的核心是对行动动机的理解和把握,而动机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动作经验,一个康德式动机可以由愿望与相应的动作经验结合而产生———如果感觉神经系统是纯粹理由运行的生物学背景,那么,康德式动机仅仅依赖完好感觉神经系统即可发生的现象就说明了纯粹理由可以是实践的。休谟式动机论可能比康德式动机论更容易得到如Libet实验一样的神经生物学事实的支持,却可能导致消除主义的挫败;实践知性两种状态的区分可以重新说明Libet实验,并为康德式动机论提供辩护。
实践知性与控制理性颜青山教授表明,实践知性诉诸自动的完全理解可能取消理由的作用,因此,最后要阐明它与理性的关系。它需要并支持一种控制理性的理性观念,将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则看作一个禁止性原则,它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理性原则。在理性问题上,实践知性两种状态的区分可以回应Greene实验对康德主义的挑战。最后,比较行为学的证据支持尝试理解在人类动作学习中的优势地位,完全理解只是尝试理解的手段。(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姚文丽整理撰写)